“言意”之辩及其语言哲学的意义
2014/9/7 热度:430
魏晋玄学,作为一种富于哲学思辨、富于智慧和热情的哲学流派,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玄学是从哲学本体论高度回归老庄哲学,在政治哲学方面仍以儒家名教立论,尊崇孔圣,因而具有儒道兼综的特点。可以把玄学看成是汉代儒道融合和互补的合乎规律的发展结果。玄学围绕着“有无”、“动静”、“体用”、“言意”等抽象哲学范畴而展开。其主要论题“有无动静”之辩是在本体论方面讨论如何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与这一中心论题密不可分的另一论题是“言意”之辩。这个问题涉及宇宙本体能不能用名、言表达的问题,也涉及到语言的功能和局限性等语言哲学的问题。过去一个时期的中国哲学研究,从知识论哲学的思维定势出发,在解释和评价“言意”之辩问题时,过高地评价了以欧阳建为代表的“言尽意论”,而否定或基本否定王弼、稽康等为代表的“言不尽意论”。给王弼的“得象忘言”、“得意忘象”、“言不尽意”贴上神秘主义的标签。这样实质上就等于否定了中国古代语言哲学所蕴涵的深刻意义和丰富内容,抹煞了中国哲学对世界语言哲学方面的独特贡献,因而也就贬低了中国哲学的地位和影响。笔者不能苟同学界某些贬低“言不尽意”的观点,试图对“言意”之辩及其语言哲学的意义,提出自己的理解和看法,请诸位时贤批评指正。
一
言意问题和名实问题,都是语言哲学,但中国古代主要是从语意方面而不是语法规则和逻辑规则方面研究语言的。在先秦主要是从名实问题上讨论“名”(名称、概念)如何表达“实”的问题。旨在揭示名称、概念和它反映的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稷下道家学派就有关于名实问题或形名问题的比较完整的论述,提出“物固有形,形固有名”“以其形因为之名”“循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名实相生,返相为情”(注:《管子·心术上》、《九守》。)等观点。战国时名家公孙龙专门写过一篇《名实论》,说:“天地与其所产者,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夫名,实谓也”“审其名实,慎其所谓,至矣哉!”(注:公孙龙《名实论》《指物论》。)说天下充满着各种事物,物所以成其自身而不超过的那个形色实体叫实。“名”是来称谓“实”的,因而要审察名实,谨慎地称谓。公孙龙还写有《指物论》,主要是研究概念与对象关系的。“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注:公孙龙《名实论》《指物论》。)说天下万物无不经由指认,指谓而定出名称、概念的,这种名称、概念自身并非所指之物或对象。这都没有超出名实关系的范围。荀况著有《正名》,也集中讨论名实关系。为什么要有名?他说:“异形离(异),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因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注:《荀子·正名》。)战国时社会处于剧烈变化中,名实错乱,名不副实,贵贱不明,同异不别,所以要“正名”。这种“正名”的思想是从孔子那里来的。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注:《论语·子路》。)因此先秦的思想家研究名实问题,主要是着眼于政治的,孔子把“正名”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政治主张联系起来。荀况的“正名”是为了“明贵贱,辨同异”,而不把语言、概念看成是单纯的符号、工具,不是着眼于语言本身的研究。韩非提出“循名而责实”“形名参同”(注:《韩非子·定法》《杨权》。)主要是考察官员尽职尽责的问题,看能否做到职分之名和实际政绩统一起来。名实问题转向政治法治是为刑名之学。言意问题和名实问题相通,侧重讨论语言、概念与其所表达的思想之间的关系,如语言能不能充分地表达宇宙本体,能不能通过语言、概念把握事物的本质,语言有无局限性,离开语言等表达形式,思想是否存在等深层的问题。如果说名实关系讨论的是“所指”“物指”的问题,那么言意关系讨论的是“能指”或“不能指”的问题。言意关系从先秦开始讨论。《易传·系辞上》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是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注:《易传·系辞上》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易传》先承认“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但又肯定“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言虽不足以尽意,而是通过立象来尽意,补救言之不足。什么是象?“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颐,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注:《易传·系辞上》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这是运用形象思维来尽圣人之意。在意的显现方面,“象”较之一般的“言”有更大的优点,比逻辑思维给人以更大的想象空间。中国的象形文字,更便于抒发人的情感和思想的不可穷尽的意义。特别是汉字以形义联结为特点,所蕴含的审美价值,是西方文字所没有的。这样《易传》既肯定“言不尽意”又承认“象以尽意”把言和象联系起来。在中国哲学史上真正提出语言哲学并加以深刻论述的是道家哲学。《老子·第一章》开宗明义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注:《老子·一章》《十四章》。)“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含有宇宙本源和普遍规律双重意思。“道”作为宇宙的本源,是无形无象的,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注:《老子·一章》《十四章》。)故“道”是不能用语言和名(概念)表达的。“天地万物和它们的规律都是可道可名的,而“道”则是不可道不可名的,因为一旦可道可名,就成为一般的经验事物,就是有限的,确定的,而“道”是无限的,无确定性的。宇宙是无限的,而无限运动着的宇宙的总规律,是任何一个发展阶段上的人所不能完全把握的。所以说反映宇宙总规律的道是不可道不可名的。如果有人号称已经发现了宇宙的初始和宇宙的总规律,已经发现了终极真理,这是多么浅薄和幼稚,是根本不懂得认识的辩证法。”(注:拙作《老子道论的理解和诠释》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 “道”不可道不可名,不在我们人类已有的知识经验之内,所以可以称“道”为“无”,但“道”作为一种总体性存在,又是确实的存在,我们虽然不能具体说“道”是什么,但确信世界上有一个初始的本源性存在,有一个贯穿万物的东西。这是老聃所承认的不能用语言和概念完全表达的唯一的东西即“道”,但老子还是强为之名,称“道”为“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注:《老子·二十五章》。)“道”“玄而又玄”,故“言不尽意”为老子哲学逻辑所固有。庄子作为战国中期道家的卓越代表,承认老子的“道”是不能名言的。他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刑之不刑乎,道不当名。”(注:《庄子·知北游》《齐物论》《天道》《外物》。)庄子对言意关系作了深入探讨。说:“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着,不可以言传也。”(注:《庄子·知北游》《齐物论》《天道》《外物》。)他把名言作为得意的工具,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注:《庄子·知北游》《齐物论》《天道》《外物》。)中国的圣哲,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提出了可道可名与不可道不可名的关系问题,接触到语言的功能性和局限性等问题,即使在今日也是非常精深的哲学问题。把这种理论一概斥之为神秘主义,是没有真正理解中国语言哲学的内容、精神和意义。以这种片面性的观点看待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辩,也就不可能了解玄学思潮中“言不尽意论”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所达到的理论高度。
二
言意关系是魏晋玄学热烈讨论的问题。在汉未臧否人物的“清议”和魏初“才性之辩”中都使用了“言不尽意”的方法。魏晋时最早提出“言不尽意论”的是荀粲。《魏书·荀@①传》说他“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粲兄俣难曰:‘《易》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粲答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及当时能言者不能屈也。”(注:《三周志·魏书·荀@①传注》。)在“言意”之辩中,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王弼、稽康为代表的“言不尽意论”;一是欧阳建为代表的“言尽言论”。稽康写有《言不尽意论》,但已佚。在他的《声无哀乐论》可以看出他主张“言不尽意”的端倪。“吾谓能反三隅者,得意而忘言”,“知之之道,不可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于马,而误言鹿,察者故当由鹿以知马也。此为心不xì@②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证心也。”(注:稽康《声无哀乐论》。)他认为“心之于声,明为二物。”稽康看到并强调了声音对于情感的表现具有不确定性,他从“大音希声”的根本观点出发,以为无哀乐之声最能表现各种复杂的情感,反对把声音局限于某种具体的哀乐形式之中。与此相似,他也认为“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趣举一名,以为标识耳。”(注:稽康《声无哀乐论》。)语言不过是一种符号,并不能完全表达思想和情感。王弼是最著名的玄学家,他主张“言不尽意”。他认为“道”不可言,不可名。这一点和老子一致,而且更加强调“道”的虚无性。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注:王弼《论语释疑》《老子指略》《魏志·钟会传注引王弼传》。)“道”“弥沦无极而不可名细,微妙无形不可名大”“言之者失其常,名之者离其真。”“故”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注:王弼《论语释疑》《老子指略》《魏志·钟会传注引王弼传》。)“道”作为最高的本体是不能用语言和概念来把握的。正如冯友兰先生说的,王弼的“体无”,并不是指对宇宙本体的把握,而是指一种精神境界。也就是以“无为心”的境界(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牟宗三先生也指出,道家“无”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目的在于提炼“无”的智慧以达到一种境界。(注:牟宗三《才性与玄理》。)不能从对象性的知识论立场和实体性的观点看待“道”或“无”,它主要不是从宇宙生成的自然规律来讲的,而是从无限与有限的关系上,针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来讲的,目的是对理想人格作本体论的解释和建构,超越有限而达到无限的一种自由境界。在言意关系上,王弼把语言看成是体悟圣人之意的工具。他在注释《周易》中,以庄子的“得意忘言”“言不尽意”来解释言(卦辞、爻辞)象(卦象)意(圣人之意)之间的关系。他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注: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王弼肯定言是来表达象的,象是来尽意的,承认言、象有尽意的作用。这也就承认了语言的功能,承认了语言、概念是表达思想的媒介。但他又进一步说:“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注: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只要得象,就可以忘言,只要得意,就可以忘象,因为言,象只不过是得意的工具,只要得意,就达到了目的,就可以把工具抛开。如果不忘言、忘象,仅仅停留在“存言”“存象”的表层,那么这种言、象就成为一种外壳,没有用处,就失去了媒介的作用,丧失了明象出意的功能。故“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注: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王弼的用意是要人们不要停留在言、象的表层,研究《周易》的根本任务是通过言、象这种媒介去体悟圣人之意,去抓住事物的根本,了解事物的深意,重在体会那种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这对停留在言、象表层,大搞繁琐章句和象数之学的汉儒,是一种深刻的批判,开辟了解《易》的一代新风。他举例说:“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注:王弼《周易略例明象》。)他的结论是“得象忘言”“得意忘象”“言不尽意”。王弼强调不执著于名言,名言不能充分完全地表达思想。世界上存在着不能用名、言表达的东西。他看到了语言符号的相对性和局限性,注意到常常为人们所忽略的语言与其所表达的思想之间的差别、矛盾,从而把语言和思想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动态的充满矛盾的活动过程,而且认为作为最高本体的道即“无”,是不能用语言,概念表达的,这是十分深刻的。“言不尽意”也揭示了全部艺术审美的奥秘,即在其无法言传而又非言传不可。美的境界,也往往存在于语言所表达的事物的表象之外。那种认为王弼的“得象忘言”“得意忘象”“言不尽意”是认识论上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诡辩,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独断之词。
在“言意”之辩中,“言尽意论”的著名代表是欧阳建。他写有《言尽意论》,主要内容是:事物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依人们对其“言”称为转移。“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以彰。然则名之于物,无施着也;言之于理,无为者也。”(注:欧阳建《言尽意论》。)他肯定语言名称对于交流思想,辩认事物的作用。说:“古今务于正名,圣贤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注:欧阳建《言尽意论》。)他还认为客观事物是变化的,语言、名称也随之变化。“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苟其不二,则言无不尽矣。”(注:欧阳建《言尽意论》。)欧阳建的“言尽意论”符合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认识习惯,肯定语言充分表达思想的功能,这诚然是基本正确的,也是人们根据朴素的经验能够接受的。语言文字是人们在劳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声音符号系统,没有它,思维活动和交流是不可能的。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离不开语言。但是语言一经产生,就有其相对独立性。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尤其是王弼等人对语言的相对性、局限性,对它的负面作用,有深切的体会。而欧阳建只承认语言表达的功能,而没有看到语言还有不能完全表达思想的一面。因此他的“言尽意论”并不能驳倒“言不尽意论”。他不了解更为深层的问题,如作为宇宙本体的道的表达问题,而道属于非名言领域。现代逻辑语言哲学认为,在科学的领域内,在知识问题上,对于确定的外界对象,可以通过语言和逻辑的形式陈述和表达,而且要求陈述的清楚性和逻辑的明晰性。但对于形而上学的问题,对于诸如信仰、自由、上帝、物自体这些科学和逻辑所不能解决的,不能表达的非名言之域的问题,则不要求表达和论证。传统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在于对不可说者,硬是要说而且装出科学的面目出现,因此现代语言哲学拒斥形而上学是有理由的。在这方面,现代语言哲学的一些观点和中国古代的“言不尽意论”有相契合之处。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一个时期完全肯定并高度评价了欧阳建的“言尽意论”,说什么欧阳建的“言尽意论”,抓住了“言意”之辨的核心理论问题,清算了贵无贱有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和经虚涉旷的神秘主义认识论,动摇了玄学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对于中国哲学认识论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显然这种过高的推崇欧阳建的“言尽意论”,极力贬低王弼等人的“言不尽意论”,这是肤浅的,不公允的,这是没有深刻认识“言不尽意论”深邃的语言哲学的内容、特点和意义所致。
三
“言意”之辩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中国的解释学。现代解释学是探索如何通过语言使主体和客体相通,“本文”和解释者两种视界融合,从“本文”中唤醒沉睡的意义。把解释看成一种历史的活动。但是西方的解释学,通过语言,最后离开语言所表达的事物,把语言上升为本体的高度。海德格尔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伽达默尔说:“世界本身是在语言中得到表现的”“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没有语言之外的自在世界”(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国古代始终是从语言的功能性和对这种功能的局限性上把握语言的。注重语言和生活世界的联系。“言意”之辩的主要倾向之一是一定程度上对语言功能的怀疑。不仅最高本体的“道”不能用语言表达,人的某种精神境界,某种情感体验,有些达到纯熟的技艺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此外,在现代科学中,由于运用经典物理学语言描述微观客体所带来的“语言困境”即经典物理学语言(描述宏观客体的语言系统)本质上不适合描述微观客体的特点和运动状态的,而量子力学又不能以别的语言来代替它。(注:肖前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这也说明语言功能的有限性。人们往往看到语言和逻辑是人们表达和交流的工具,是认识的思维形式,而往往忽视了语言和逻辑的局限性,把语言、逻辑和思想看成是完全一致的。象欧阳建的“言尽意论”就是中国古代这方面的代表。只见同一,不见对立和差别。事实上生活中的种种欺骗和谎言,作为教条主义的表达方式的官话、大话、假话、空话,意识中的一些虚幻的东西,宗教关于彼岸世界的幻想,大量是通过语言功能表现出来的。由于语言和概念方面的岐义,造成许多无谓的分岐和争论。魏晋玄学“言不尽意论”的深刻哲学意义是肯定语言和生活世界的关系,肯定通过言、象去体会圣人之意的前提下,走着一条通过语言而又超越语言的道路。之所以如此,因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把哲学看成是洞察人生真谛的智慧之学,通过这种途径,以实现理想人生,理想人格和人生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中国哲学重视人与人之间心灵的相通,人与物相通,人与自然界相通。在运思方式上重体验,重领悟,重价值,他们不在世界之外去认识世界,而是在世界之内,把自身契入进去,主客观融而为一。在追求最高境界的过程中,往往觉得语言、逻辑反而成为体道的屏障,会造成对真理的遮蔽,产生思想的因循、僵化、片面、断裂等等。这在中国佛教禅宗那里达到了极端化的发展。他们倡导不立文字,不读经文,不拜佛像,靠“棒喝”“机锋”和隐喻,去体悟“自性真空”的佛教真谛。中国古代许多哲学家不重视逻辑本身的问题,并不是意味着中国哲学家的表达和论著不符合人类思维的逻辑规律,这一点金岳霖先生曾说过:“中国哲学家没有发达的逻辑意识,也能轻易自如地安排得合乎逻辑;他们的哲学虽然缺少发达的逻辑意识,也能建立在已往取得的认识上。”(注:金岳霖《中国哲学》《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
从知识论哲学立论,把哲学看成是追求关于外在对象的知识和经验的科学,那么在思想和语言的关系上必然是“言尽意论”,即任何事物实体可以陈述,可以用逻辑的方法求证。如果把哲学看成是追求人生境界的学问,看成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看成是信念之学,那么在语言和思想的关系上只能是“言不尽意论”即人的精神境界,信念信仰的问题,是不能完全用语言表达的,也无法用逻辑的方法证明。“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注:《庄子·天道》《庚桑楚》《徐无鬼》。)“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注:陶渊明《饮酒二十首》。)语言本身是体道的媒介,既然已经体悟到“真意”,则语言就成为多余的外壳,故可以“得意忘言”。中国古代许多哲学家主张由“辩”到“不辩”,由“言”到“不言”,才能真正体悟到最高本体的“道”,才能进入与道为一,天人合一的境界。老子讲“致虚极,守静笃”,“玄鉴”(注:《老子·十六章》。)稷下道家讲“静因之道”“洁宫”“去囿”(注:《管子·心术上》。)荀况的“虚壹而静”(注:《荀子·解蔽》。)都有排除语言和外物干扰,靠直觉达到体道目的的意义。
承认了“言不尽意”即语言的一定的局限性,也就承认了语言在表达事物和思想方面的不确定性,模糊性。中国古代一些真正哲学家的思想,往往是用诗的形式表达的。诗即哲学,哲学即诗。诗固然离不开语言,但诗的深邃思想和美学意蕴往往存在于语言所表达的形象之外,所谓“意在言外”,“此地无声胜有声”,“言有尽而意无穷”。中国艺术讲求“意境”,有无“意境”,成为抒情艺术的最重要的标志。这与西方哲学某些学派以语言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去割断与生活世界的联系是完全不同的。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否认语言符号反映世界的功能,语言不再是传达思想的工具,把事物之间的联系抽象为语言与语言,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变换游戏,它是唯一的对象,它是思想本身,它就是世界,这种脱离了社会生活的语言和文字符号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这种语言哲学,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是反映了当代西方一些人的躁动的虚无主义思想倾向。(注:郑家栋《走出虚无主义的幽谷——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辩异》《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魏晋玄学“言不尽意论”的深刻意义还在于这种思想和世界上一些大哲学家的思想有若干契合和相通之处。康德哲学承认“物自体”在纯粹理性的范围内“不可知”,这是为了肯定实践理性的地位高于理论理性,是为了给科学划定地盘,使科学不要奢望去解决自己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不过康德给科学划定地盘,是为了给宗教信仰以崇高的地位。而中国的“言意”之辩中的“言不尽意”并不是贩运哲学不可知论,不是给宗教信仰留出地盘,而是在追求人生的一种精神境界和塑造理想人格,表现了一种理性主义精神。当代大哲学家海德格尔承认“无”,承认有不可说者,认为这是最高的境界,只有通过“无”,通过不可说者,才能真正的把握存在,而语言的表达往往会造成对“存在”的遮蔽。逻辑实证主义大师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前期著作《逻辑哲学论》中,考察和批判语言,其最终目的是要给语言划定界限,分清什么是可说的,什么是不可说的,主张对于不可说者不要说,“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应该沉默”(注: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导论》。)这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言不尽意论”。在他的心目中,形而上学是在语言之外。他虽然认真地进行着科学逻辑的语言分析,实际上也是在科学和信仰之间划定界限。他之所以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是因为对于本不可说的东西,硬是要加以言说,这是不允许的。中国古代的“言不尽意论”及中国的语言哲学,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也体现了中国哲学家运思方式的特点。我们只有站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上,才能看出魏晋玄学“言意”之辩中“言不尽意论”的深刻哲学意蕴和对于艺术的创造和鉴赏的不可估量的意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或加多加一撇
@②原字为系的繁体字
(原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1期 作者系西藏民族学院政法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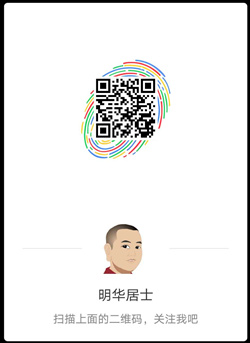
电脑上扫描,手机上长按二维码,进入明华学佛微博,点关注
五明学习: 声明: 语言 | 音乐 | 文学 | 声明 | 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