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呗与佛教音乐(下)
2014/9/7 热度:352
佛教音乐藉由转化意义与实践,取消了梵呗的在地性, 却无法取代其无法被消费的领域—梵呗或梵呗的寺院功能, 它们皆有历史特殊性,以建构文化的认同,引发不同的实践与经验。 现代主义、佛教音乐与政治 十九世纪以降,中国佛教寺院传统采用‘音乐’一词,以联系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运动。从此,‘现代化’对多数的中国人而言,已成为一个文化的视野,是巩固国家的基础,也是一个政治计划,以打破传统而开始另一种新生活的方式。 然而,中国社会在现代化的文化转化过程中,实呼应了西化与技术统制。‘现代化’为佛教与社会、僧团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带入深远的转化。 [社会运动与改革,转变寺院文化与政治次序] 现代国家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深化了寺院的文化与政治次序的转变,这转变的过程反应在许多运动中。于其中,创发‘佛教音乐’一词以取代寺院‘梵呗’,正呈现了一个寺院文化实践上的重大概念转变,套用一句罗伯特?杨(Robert Young)的话,这名词‘保存了文化接触的历史状况’。 十九世纪以来,清廷一连串战事上的挫败,以及后续的社会与政治危机,迫使中国人启开对‘现代’与外国的接触:新的社会与政治意识型态、新文化计划、新政府组织、新军事装备、新科学信仰、新宗教、新教育系统等。经由不同的社会运动与政治改革,这些接触承载着各类现代化的计划,许多传统寺院实践和规约,也受到这些事件与运动的直接影响,而导致衰微或产生剧烈的转化。 在僧团开始感受到现代化的影响之前,中国佛寺传统的许多特点仍然持续着。例如寺院是佛教活动的中心,僧伽是主要领导宗教活动的人。传统上,十方丛林由所有僧伽所共有,僧伽的日常生活由丛林清规所规范;另有一些小寺院,由该寺院的僧伽代代相传经营维系。民国建立以前,僧伽可免于赋税、劳役与征召入伍,也无须向皇帝礼拜。 辛亥革命之后,清廷对寺院的保护与赞助也随之结束,佛寺面临被没收,以作为学校或政府办公室的威胁,而寺院的耕地也遭到充公以支付教师的薪资(Welch 1976: 167)。在这段期间,许多佛寺为了自保,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学校(即佛学院),以提供僧伽(尤其是年轻的僧众)有关佛教、科学、文学、历史与现代学科的教育。其他重要的自我卫护方式,包括建立中国佛教协会,透过众多佛教徒有效地游说以保护寺产;建立孤儿院、诊所与慈善、宗教机构,以促进僧团与社会的关系。 虽然僧团已做了某种程度的改变,以调适其在现代社会的地位,然而阻碍与威胁似乎并未停息。在中国,反宗教的运动于一九二二年开始展开,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对寺院文化和规约的破坏更甚于前朝。在台湾与中国的新政府于文化建构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社会关系趋于由政府来管理的情况遽增,是当代社会与政治生活无法回避的视界(Bennett 1998: 61)。赋税、司法、福利、军事与其他势力,在以往多属于地方管辖,而现在则由国家政府管辖(Zhao 2001: 11)。国家的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以及新推行的宪法制度,皆重新定义了政治的分界。僧团自治的分界线,在现代国家的政治系统中已大感局促了。 现在,文化领域逐渐增强为政府组织管理与建构的成分,政府的文化政策往往成为国家与文化关系结构的主要成分,这是现代化社会的特色(Bennett 1998: 4)。然而,在许多社会里,有时政府与社会菁英名流明显地扮演了如殖民者的势力,藉‘现代教育’之名,在地方习俗与语言上,强制输进他们自己的规定和语言(Tiyaranich 1997: 66)。新的社会与教育发展,并非皆产生自人民的需要,它们透过强化的政策与军事力量的结合,以及一套西化的教育系统,而强加在人民身上,这状况在台湾与中国的许多社会族群中显而易见。 二十世纪中,中国佛教僧团由与其他社会族群的文化交流和社会化中,改变了传统的宗教实践。现今许多透过现代教育与社会化,而塑造出宗教智识意象的佛教徒与非佛教徒,常常持着挑战寺院传统的观点,他们认为传统上寺院僧伽所必备的知识,如梵呗、仪轨、烧饭、威仪与禅坐,皆是较次于现代学科的课程,而这些传统课目在当代佛寺中,也已大量缩减。 [资本力量全球化,重塑僧团的社会关系与文化生产] 中国佛教僧伽所遭遇的巨大现代化冲击,也包括帝国资本力量的全球化,以及遽增的大众传媒的跨国流动,这些全都重塑了僧团的社会关系与文化生产。罗伯特?杨认为帝国资本力量的全球化,已在这世界强制地输入一个统一的时间,这力量是建立在破坏人们与文化在地性的代价下而成就的。以中国佛教传统为例,寺院长期使用具在地特性的名相称号与文化实践,对其他的社会成员而言,已渐渐变得遥远、怪异。因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概念,已经由现代教育系统与大众生产的跨国的文化实践所取代,人们渐渐地更加熟悉于那些外来输入的概念与实践。 梵呗与音乐这两个语言的意识运作,显示了当代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些挑战与社会化过程,在组织一个政策与社会经营的特定领域里,再现了特别的寺院文化的论述,这些意识也与其他社会运动产生了联系。 [以佛教音乐作为佛教复兴的计划] 对某些佛教徒而言,佛教音乐的使用,为佛教复兴运动带入生产性与论述性的方案。在此,复兴并非指重建佛教的传统,而是藉由佛教的现代化,以促进佛教的普及。对如此主张的复兴运动者来说,音乐比梵呗更适用于现代化的场域,因它联系了当代社会的语言形式与其支配的机制。更重要的是,它联系着欧洲使用的语言。音乐—这个新的语言类目,现今已译入政策的过程中,其中寺院的文化资源被运用,以展示于现代社会的环境中。 例如,台湾佛光山创办人星云法师,便认为寺院梵呗具有重要的弘法功能,应在现代社会中大力提倡。星云法师曾致力于促进僧伽与社会的联系,他不仅尝试将寺院梵呗传统推广到在家信徒的团体中,也鼓励以新的佛曲创作来弘法。佛光山曾出版多种梵呗与佛教音乐录音产品,以及创作的现代佛教圣歌,近来又设录音室,并举办佛教音乐会,由出家与在家众共同演出。事实上,星云大师的佛乐与梵呗现代化,是承续了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佛教的复兴运动。当然,佛光山并非是第一个启用新的佛乐形式的佛教机构。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就已有佛教梵呗的录制,并经由电台广播等大众传媒介绍给社会大众,许多现代佛曲也皆由僧伽与在家居士所创作。 如二十世纪初,最重要的佛教音乐创作者弘一法师(1880-1942),其创作的佛曲歌词法意深远,而旋律则以西方大小调为基础,或改编自西方的民歌。这些佛曲皆有近百年的历史,在中国佛教徒中仍是最具影响力且最受欢迎的音乐作品。‘佛教音乐’在当代中国寺院内外已渐成为一个公认的概念与实践,现今在台湾与中国大陆,许多佛教机构皆曾发行梵呗或现代佛乐的录音带、歌本。佛教音乐——一个社会化的客体,打破传统寺院规范的界线,争取了建立新的论述与实践的自主性。 思想之战 一个影响社会的新观念,其能改变社会的力量,绝非单纯经由文化概念的散播而来,而是经由中介的结构,如社会运动等(Homans 1995)。如容格(Carl G. Jung)所述,运动与内在奋争,是决定新概念未来是否能成功的基点(Homans)。当代中国佛教,以‘音乐’指称传统仪式唱诵,并出现现代音乐实践(如生产流行与商品佛教音乐,以及佛乐的舞台表演等),皆涉及了各种政治与宗教运动。‘佛教音乐’是一个新的文化生产与论述类目,以带入新的成员与观众参与其建构过程,并使寺院音乐实践进入一个新的文化再现领域。 [佛教音乐的实践,带入不同的文化概念] 然而,这个文化再现的过程并非顺畅容易,佛教音乐的文化实践从未孤立发展,从它一开始打破传统的概念,并涉入政治与意识型态的斗争时,便充满冲突与矛盾。在僧团中,针对寺院的音乐实践,为了是否需要保存或改变此传统的寺院规范,已产生了各种意见与政策,且各地寺院音乐的文化生产的差异性也逐渐增加,使僧团制度的建立与教育功能更加具体化,同时也联系了寺院与社会的关系。 无论是依据传统规约以规范仪式与音乐的施行,或更动仪式内容(删减或更换仪轨内涵),或将寺院仪轨商业化,皆构成了不同的文化概念与社会意义。梵呗、音乐,甚至商品与流行佛教音乐,都个别形成不同的族群价值。当然,它们也含纳了不同的仪式效益,以建立教义范例与个人的宗教认同。 ‘佛教音乐’这个论述类目在寺院内外创发了不明确性,和多种音乐形式与诠释方法。今天,如此不明确性与多样性急遽增加,而世界的转变也与现代的文化生产、社会生活深刻连结,其技术与概念的发明既快速又广泛。新的文化生产状况影响寺院音乐的实践,包括仪轨意涵、功能与运作,同时又创造了不同的排拒与接纳的面向,以及社会关系。我们应认知到,音乐领域与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状态的关连性,与其相互影响所呈现的一连串地方文化的意涵与政策的反应。 [佛教音乐同时连结又分离于寺院传统] 罗伯特?杨与汤尼?本耐特(Tony Bennett)观察全球帝国主义与资本势力对地方文化的影响,认为在这些力量的影响下,文化从未倾向固定、停滞或有机整体的呈现。而是文化与文化区分不停地建构及再建构,因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均衡状况下,内部的分歧不断产生(Bennett 1998)。今天,在中国,尤其是在台湾,中国佛教梵呗(犹如摇滚乐或民歌等许多其他乐种),在社会进程中,已妥协并扭曲了佛教梵呗的原始音声价值。 佛教音乐是结构于一个复杂的文化接触、侵入、融合与分裂的历程。这个文化概念并非存在于任何特定的旨趣中,或独立自成一个完整的个体,而是存于一个辩证的结构中,在建立其社会性的同时,并接受其他观点的批判,它本身即是一直处在分界与分离的状况。本来源于佛教寺院传统的当代佛教音乐,在概念上与实践上也是如此,它同时连结而又分离于原生的传统。诸类的佛教音乐(世俗或宗教的,修持用的或商品的),在同一名目下,透过各式的生产、使用、消费、编制与表现方式,进而不断地制造与发展。 不同的语境造成音乐实践的不同意义,由参与仪式所产生的佛教梵呗,即不同于音乐会或录音带中的梵呗。每一类佛教音乐都是以其独特的方式,在其所建构的要素中创造意义,事实上,它们已各自形成不同的文本了。不论在梵呗、音乐或商品佛教音乐中,语言的使用在在体现了其自我的世界,每一类目不断强调特有的功能与矛盾,并且轮流地取得优势。 在佛教历史的运作中,既存的文化类目外化或对立现象(如佛教音乐或商品佛教音乐之相对于梵呗),通常都可能慢慢转化而成为该文化的一部分。罗伯特?杨的后殖民主义,视文化实践的同异区分,是文化建构的可能性,多于为矛盾与冲突的基点(1995: 30)。他解释:文化是一辩证的历程,刻入与排除自己的转化。‘文化’概念的历史揭示它并非是个进步的过程,而是不断地在冲突分界上自我修正,参与并属于一个组合,而混成组织的一部分(1995: 30)。这里‘混成’的概念是不断重复的,因它强调了在一语言中具有多重意义的性质:‘语言根本功能的状况是异同共存’(1995: 20)。杨应用了巴克亭(Bakhtin)的概念,指出‘混成’(hybridity)是两个不同的语言意识,在同一发声的竞技场上遭遇,彼此为时代、社会所区分,或其他因素而分离。 尽管‘佛教音乐’这名词可能渐趋同质性的发展,意识形成与文化实践,总是因不同的社会族群与个人而有区别。关于音乐实践与佛教僧团组织的关系,与佛教于社会关系上的经营,我们都需要考虑到它们在佛教的理解与经验上所造成的影响,尤其宗教与音乐经验涉及许多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功能和知识。音乐或文化类目的在地区分,不应因较独断分类的现代文化观点介入,而受到忽略。即使有一些佛寺,如台湾的佛光山与香光寺,曾制作录音或商品佛教音乐,但其僧伽都清楚了解,不同的音乐实践将导引不同的宗教实效与经验。 佛教、音乐实践与寺院文化认同 [梵呗引导人们了解经验的本质] 佛教教义最初由佛陀(意为觉者)所教导,佛陀能成就其圆满智慧,并非由阅读或谈论,而是由自己的经验获得。经过了两千五百多年,佛教徒已建立了系统且实证性的方法,作为直接的经验与印证,这些方法也多是开悟者所亲证的智慧。不同的佛教传统建立起大量的宗教修行知识,以作为人们在其特别环境的修行根据。许多佛教传统皆具有次第、进展性与明确的修证方法。但是,佛教的真实性仍然无法由一个静态的传统而呈现。约翰?皮克林(John Pickering) 曾说,除非在个人的经验中印证,否则佛教对个人而言,并无真实性的存在(Pickering 1997: 31)。 佛教徒被教导要亲自己去思惟,体验日常生活,并经历其见闻觉知的根本转化。佛教仪轨,除了反应群体和谐的功能之外,也帮助僧伽对教义的了解。中国佛教仪轨含括特殊的技巧与哲学,以引导梵唱者了解人们经验的本质。例如,由专注于即时、自发的梵呗当下,僧伽观照五蕴(色、受、想、行、识)在一个相互关连状态的存在中生灭。唱念时,僧伽见梵呗不是一个统合的事物,而是动态进行的过程。这是为何中国佛教梵呗包含自由念诵,及允许唱念者自发性地诠释梵呗,以反观身心状况的原因。 [梵呗与佛教音乐的争论,重点在其所呼应的群体功能与机制意义] 中国佛教寺院仪式传统的建立,具有多重的功能。僧团音乐概念与实践方式的演变,部分反映了此传统在政治纷争或社会经营中,所要达成的不同目标。从一开始,中国佛寺的仪轨便采用许多在地的音乐素材与宗教习俗,明显的例子是,仪轨中包含有赞、偈、曲牌、旋律牌与仪式程序,这些都清楚显示,它反应佛教在地方需要与已建立文化之间的调和。实际上,仪式提供了一个沟通的空间,让群体能够参与。因此,仪式的实践,除了再现佛教教义论述之外,也反应于宗教的对象,包括宗教修行者、信徒、未来的信徒与整个社会。并且,仪式实践无法从人类存在与关系的主要考量中分离,而这些当然都有其历史的特殊性。 在僧团的语境中,多数关于寺院梵呗与通俗佛教音乐的争论,重点都在于其所呼应的群体功能与机制意义。若任何新的名相与实践,皆不影响如此的功能与意义,则无须对任何寺院规约、文化建构等议题进行辩论。相对地,若佛寺仪式传统与社会其他音乐传统无有差别,僧团便无须费力以创作属于其特别形式的音乐。 然而,僧团的生活视域与形式,皆依佛陀的教示而建立,而非社会的习俗,但这并非要求寺院生活与文化结构,要与社会惯例全然分立。既然宗教信众来自于社会,那么僧团组织、历史与文化次序,就和社会相互关连。寺院文化在实践上虽是经过拣择而建构,但仍然与社会的文化进程紧密联系,只是透过拣择的过程,寺院传统积极地塑造其特殊的文化认同与实践形式。 当代中国佛教寺院传统的塑形力量,实际上连结了当代社会与历史的变迁,其中政治、文化、意识与经济结构经历了极大的转化,而在寺院仪轨实践中,结合当代社会的重要文化要素,已成为定义‘佛教音乐’的一个因素。我们应注意到,‘佛教音乐’出现于当代中国佛教寺院,不仅只是一个概念,它也制造了问题,不但使议题变得具体,而在发展后,也呈现了矛盾。 [消费性的、再现的佛教音乐,创造了与梵呗不同的生活体验] 佛教音乐—一个社会化的方案,将寺院传统与社会的支配文化实践连结起来。首先,包括佛教音乐在内的所有音乐皆可消费,而出现了介于不可消费的性灵陶养,与可消费的音乐再现的矛盾现象。 商品佛教音乐在台湾、中国、香港与世界其他地区陆续生产,内容涵盖寺院梵呗、梵呗编曲,或依于佛教故事与含佛教主题的创作曲,或具佛教的想像气氛与隐喻的创作曲等。在这些发行中国佛教音乐的地区,人们以主流文化的消费方式诠释佛教音乐,其中最普遍的再现形式是,将佛教音乐描述成来自遥远而奇特的文化,或是清净与真实的象征。从这点来看,这些商品佛教音乐的生产程序与消费实践,与其他类别的音乐并无不同。正因其形式是消费性的、再现的,而使佛教音乐创造了一种与寺院梵呗不同的生活体验。 佛教音乐藉由转化意义与实践,取消了梵呗的在地性,但是却无法取代其无法被消费的领域—梵呗或梵呗的寺院功能。这两类目皆有其历史特殊性,以建构文化上的认同,并引发不同的实践与经验。文化与个人认同是透过语言而建立的,佛教音乐是介入一既定认同的文化类目的方式,它在认同政治的沟通过程中,融入了现代佛教与文化的表现,同时也在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中,撞击了宗教实践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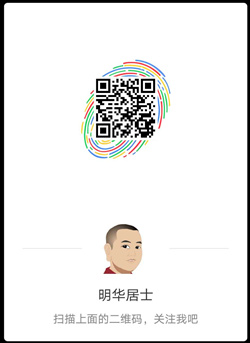
电脑上扫描,手机上长按二维码,进入明华学佛微博,点关注
五明学习: 声明: 语言 | 音乐 | 文学 | 声明 | 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