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與中國印刷
2014/9/8 热度:519
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經中華民族增加一份堅強無比的活力。這在民族生活的各個方面皆表現得異常明顯,而對於印刷術,尤其彰著。 古代印度的佛經,開始只是師徒相承,口語相授,並無見諸文字。直到公元前一世紀第四次結集時,才把經文和注疏化錄在棕櫚葉上,成為卷帙浩繁的三藏經典。梵文稱樹葉或葉片為「pattia」,音譯為「貝多羅」,因此便把這種記錄在棕櫚葉上的佛經簡稱為「貝葉經」。它的裝幀,類似我國古代的竹簡,用細繩一片片串成。用棕櫚葉製成一部經書,要經過採葉、水煮、晾乾、磨光、裁割、打洞、畫線、刻寫、上色、裝訂等十幾道工序,十分麻煩費力。 佛教傳入中國時,我國尚無印刷術的發明,但已有紙張出現。到二世紀初,蔡倫改進造紙術,用樹皮、破布、廢網等造紙,紙質堅韌,造價便宜,於是「天下咸稱蔡侯紙」。所以,我國翻譯的佛經就可以抄寫在紙上,這比刻寫在棕櫚葉上方便多了。但抄寫佛經並非易事,特別是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佛經的進一步發展,上至貴族,下至平民,信仰佛教的人很多,需要的佛經數量更大,僅靠抄寫不利於佛教的傳播。 我國商代刻甲骨,先秦雕印璽,秦襄公刻石鼓,秦始皇封禪勒石,漢蔡邕令學生摩拓經文,魏晉道家制符篆,晉代反寫陽文磚誌,南朝梁反刻念文神道石柱,以及陶瓷的印花,絲質的鏤板印花,都表明人們刻學技術的不斷提高。而創自東漢,發展於魏晉的松煙製墨,以其不會模糊漫漶而成為印刷技術產生的必要條件。 佛教在中國傳播的過程中,也繼承了我國古代的石刻技術,六世紀中葉北齊高氏王朝統治時期已有石刻佛經,其代表作有山東泰山經石峪的《金剛經》,山西太原風峪的《華嚴經》,河北武安北晌堂山的《維摩詰經》等。到了隋代,石刻佛經大發展,沙門靜琬開始在幽州大房山石刻佛經,以後歷代繼續增刻,成為中國現存規模最大的石刻佛經。另外,寺院和佛教徒還用捺印的方法製作小塊佛像,供人作為崇拜敬奉的對象。以後又刻印一些大張佛像和律疏。相傳唐代玄奘法師曾以回鋒印普賢菩薩像,佈施四方。正是在這諸多因素影響之下,我國在隋唐時代終於發明了雕板印刷術。 迄今我們能夠看到的最早的印刷品實物,大都同佛教有關。如韓國發現的《陀羅尼經》,它澤印於武周最末一年的長安。唐末司空圖為洛陽敬愛寺僧惠確寫的雕刻律疏文,曾說印本共八百紙,可見那時寺院已有施捨用的律疏印本了。 敦煌發現的唐咸通九年(八六八年)王玠出資雕刻的《金剛經》卷子,是現存世界上最早的第一部標年木刻印書。此經用紙七張復合成卷,全長四八七七米,高○‧三三米。第一張扉頁印釋迦牟尼佛說法圖。釋迦牟尼佛坐於祇樹給孤獨園的經筵上說法,長老須菩提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面佛而言。佛的左右前後,圍站著兩員護法天神以及許多貴人施主和僧眾。經筵的前面,臥著兩頭勇猛的獅子,說明佛法無邊足以降服野獸。 圖的上部,在微風飄動的幡幢上,兩位仙女駕著祥雲而來。畫面純用淺刻,刀法遒勁,流暢嚴謹。由於處理得巧妙,自有虛實關係。畫刻者為使畫面燦爛完整,還在地面上施以四方連接圖案的氈紋樣。整幅畫的佈局結構和人物線描的技巧風格,與唐代佛畫的手法大致相同。 圖片左面,是《金剛經》文,字體勁拔,體兼顏(真卿)柳(公權)。經文後面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的題化。這件比較成熟的雕版印刷品,反映了我國當時印刷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可惜這卷舉世聞名的唐代雕版印刷的佛經,為斯坦因劫去,現存英國博物館中。 一九五四年,四川成都唐墓中又出土了一張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印的梵文《陀羅尼經》,大約一尺見方,中央刻有佛像一尊座於蓮花座上,環繞佛像印有梵文經咒,咒文外四邊又刻印各種小佛像。這件珍貴的雕刻印刷品是目前國內僅存的最古的唐刻本。 五代時期,我國的雕版印刷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當時已能雕刻整部書籍,而且多是佛經和通俗書。我國最早期的雕版印刷品,一般都不留刻工姓名。敦煌石窟藏經洞發現的刻於後晉開運四年(九四七年)的《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像,是我國迄今發現的最早的留有刻工姓名的雕板印刷品,在世界上也屬於最早。 這件雕板印刷品從三二‧一釐米,橫二三‧七釐米,白麻紙,有帘紋。正中刊印觀世音立像一軀,約佔全幅的三分之二。觀世音頭戴寶冠,腳踏蓮台,右手提花籃,左手二指相扣,三指上升作說法印。項間披帛飄舞,胸前垂有瓔珞,背光圓圈上綴以華蓋,墨線流暢生動。左側懸功德幡,文曰:「歸義軍節度使檢挍太傅曹元忠造」;右側方柱標題:「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菩薩」。施印者曹元忠為曹義全之子,官至檢挍太師兼中書令西平王。開寶七年(九七四年)招贈『敦煌郡王』。這是歸義軍統治者受到中原朝廷最高的殊勳。 曹氏三代統治瓜、沙二州一百四十多年,曹氏祖父子孫的升官進爵,在敦煌石窟的畫像上都有反映,其中以曹元忠執政時間最長,留下的遺物也最多。據《敦煌學概要》(蘇瑩輝著,台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一九六四年出版)所收插圖三之四,倫敦大英博物館藏『觀音立像』印本,下部有造像化十三行,化文曰:『弟子歸義軍節度使州沙等州觀察處置管內營田押蕃落等使,特進檢挍太傅僬郡開國侯曹元忠,雕此印板,奉為城隍安泰,闔郡康寧。東西之道路開通,南北之兇雜順此。厲疾消散,刁斗藏音。隨喜見聞,俱治福祐。於時大晉開運四年丁未歲七月十三日化。匠人雷延美。』經核對,這二件印本係出自同一板本。由此可知,此件印本的年代亦應為後晉開運四年。刻工姓名能在印本中留存,是我國印刷史上的一個重要標誌,說明當時雕板印刷術的發展和雕工地位的提高,這對後世印刷術的影響是很大的。 另一件五代雕印的《聖觀自在菩薩》像,縱二六‧二釐米,橫十八‧二釐米,楮紙。此印本畫幡,上欄雕印觀自在菩薩像,作結跏跌坐於蓮台座上,左手執蓮花,右手做說法手印。菩薩身被環繞於墨線同心圓圈中,天空灑有鮮花,菩薩身下有海浪,本尊左右兩旁置有蓮花供養字牌,左邊字牌題『聖觀自在菩薩』大字一行;右旁字牌題『普施受持供養』大字一行。下欄雕印,『發願文』十四行。此幡墨印填彩,施以紅、黃、綠三色繪,天地頭裱有寶藍四瓣花錦文圖案,格個極為鮮明典雅。雕板印畫線條清晰,字跡渾古,反映了五代時雕印技術的精良。 隨著雕板印刷技術的發明和進步,北宋太祖開寶五年(九七二年),北宋政府派人到益州(今成都)雕造大藏經五千餘卷,稱《開寶藏》。這是一次規模巨大的雕板印刷工作,開雕板印刷大型叢書之先河。『蜀本』也由此而知名。開寶八年(九七五年)吳越國王錢俶倡刻的『陀羅尼經』(雷峰塔內藏經),是現存最早的『浙本』,字體工整,和後來杭州刻的小學佛經相似。近年浙江龍泉塔下發現的北宋初年刻的佛經殘葉,字體寬博,和南宋官板書相似。可見杭州和浙江其他地區從五代末年起,已有大批刻板技術熟練的工人。這就無怪北宋監本多數都是浙本了。 自北宋木刻印刷《開寶藏》之後,遼興宗耶律宗真景福元年(一○三一年)始刻的《契丹藏》,北宋末葉刻的《崇寧藏》,兩宋之際刻的《毗盧藏》,南宋初刻的《圓覺藏》,南宋中葉刻的《資福藏》,金代刻的《趙城藏》,南宋末始刻而完成於元代的《磧砂藏》,元初刻的《普寧藏》等,也如雨後春筍般在各地印刷,反映了宋元時期我國印刷事業的興旺。 元至元六年(一三四○年),湖北江陵資福寺刻的無聞和尚《金剛經注解》,卷首靈芝圖和經注都用朱墨兩色套印,這是現存最早的木刻套色印本,對後世影響很大。到十六世紀末,吳興、杭州、南京等地書肆也用朱墨和多色套印各種書籍,使我國的印刷術顯得更加炫麗奪目。 明清兩代的南北二京,是全國刻印佛經的中心。《洪武南藏》,《永樂南藏》,《永樂北藏》和《龍藏》,紙墨之精,雕刻之工,裝潢之美,都是前所罕見的。另外,清代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年)創建的德格印經院,則是藏區規模最大的印刷中心。該院藏有各種藏文典籍的書板多達二十餘萬塊,所印書籍流傳很廣,清代刻本藏文大藏經,挍字精細,刻工優美,見稱於世,稱德格版藏文大藏經,與那唐版,北京版,拉薩版齊名。 刻版印刷雖是特殊的文化藝術之一,但畢竟太費時費力。自北宋慶歷年間(一○四一至一○四八年)畢昇發明活字印刷以後,便開始用活字排版印刷。近代漢文大藏經的流通就多採用排印版本了。 總之,佛教在我國歷史上長期流傳中,對我國印刷術的發明和發展的影響是顯著的。至今各地寺院中保存的大量古代刊印的佛經和圖書,不僅是中國文化遺產的一部分.而且也是研究我國印刷史的珍貴的實物,這是應當引起我們重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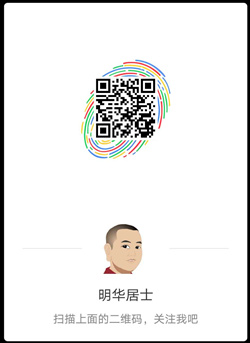
电脑上扫描,手机上长按二维码,进入明华学佛微博,点关注
五明学习: 工巧明: 地理 | 雕塑 | 绘画 | 建筑 | 历史传记 | 农工商业 | 书法 | 天文 | 舞剧 | 哲学 | 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