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的河西佛教(1)
2014/9/8 热度:667
元明清时期的河西佛教 河西地区东起鸟鞘岭,西至敦煌,南依祁连山,北靠龙首山、合黎山、马鬓山,中间为狭长地带,故称河西走廊。这条走廊,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和周围地理环境的特定关系,历史上会是中原通往西域、中亚、西亚以至非欧的必经孔道,是闻名於世的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干线路段之一。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流荟萃,民族交往十分频繁,同时又是屛蔽关陇的门户和中原王朝势力强盛经营西域的中转站,所以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第一章 元明清统治者与河西佛教 河西起廊处在青藏高原北缘的祁连山胍与蒙古高原南缘隆起的走廊北山之间,是蒙、藏进行交往的最近地区,该地亦有藏、蒙居民聚居,因此,蒙元统治者为了搞好与藏族的关系,巩固其统治,极力尊崇藏传佛教,阔端与萨班在凉州的会谈即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继后的明清统治者,为了羁糜蒙、藏,也极力推崇藏传佛教,对其进行怀柔,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第二章 元明清时期河西佛教发展概况 由于元明清统治者的热心提倡,为河西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河西地区本来就遗留下了很多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西夏时期的佛教寺院,元明清时期又重修、补修了不少寺院,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场所。再加上西夏时藏传佛教在河西一带已较流行,且已有了很好的基础,元明清时则更盛之。河西居民在此时大多信仰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他们虽然过着贫困的生活,但却慷慨解囊,支持佛教寺院的建修,为佛事活动布施,所有这一切,都足进了河西地区佛教的发展。 第二节 甘州
前言
汉代以来,佛教东渐,陆路经由西域、河西走廊,传入内地。由於近水楼台,使外来的佛教文化,在河西地区以比内地更为优越的条件而传播。早在西晋时期,竺法护就会在敦煌、酒泉一带翻译佛经,讲经授徒,影响很大。十六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争连绵,但佛教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河西地区,佛教更为活跃,译经圣行,开窟建寺成风。北魏灭北凉后,河西佛教暂时衰弱。但不久,随著北魏统治的加强,河西佛教又渐渐恢復。隋唐至宋初,河西地区由於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佛教虽也有所发展,但远不如十六国时期那么兴盛。西夏占领河西后,由於西夏统治者极力崇佛,会一度把佛教作为国教,河西地区的佛教会盛极一时。到了元明清时期,由於海上交通的兴盛,“丝绸之路”的衰落,河西地区也随之失去了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作用,河西的佛教发展衰微。但由於元明清时期,各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边疆,羁縻外族,都对藏传佛教极力推崇,河西地区的藏传佛教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汉地佛教的发展。
关於元明清时期河西的藏传佛教,藏文佛典中有大量记载,如部分藏寺志及《安多政教史》等,汉文中的资料也有少许,如明清《实录》及河西的地方志。而汉地佛教,佛籍中记载很少,洋洋百馀卷,载有千馀人的《大明高僧传》、《补续高僧传》、《新续高僧传》及《续比丘尼传》等典籍中,河西乃至甘肃的僧尼寥若晨星,显然河西的汉地佛教发展落后了。幸在河西的地方志中还载有大量关於汉地佛教的资料。
本文主要运用明清河西方志、考古资料及藏文典籍(汉译),对元明清时统治者对河西佛教的扶持,河西佛教发展概况,特点及产生的影响,作一全面考察,以明确元明清时期河西佛教的状况。
《元史.太祖纪》载成吉思汗二十一年(一二一六)夏,取甘、肃等州;秋,取西谅府搠罗、河罗等县,占领了河西。《元史.太宗纪》载,元太宗窝阔台七年(一二三五),皇子阔端奉命统兵由陕入川,收秦、巩等二十馀州,一直打到成都,后撤军屯兵镇守凉州。窝阔台死后,一二四二年,乃马真皇后专权,阔端“开府西凉”,一二五一年卒於西凉府。阔端开府西凉期间,所做的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邀请萨迦.班智达赴凉州举行会谈。
萨迦.班智达(一一八一~一二五一年),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任法王,於一二六年接替其伯父住持萨迦寺,成为当时西藏地方很有影响的一名佛教大师,萨迦派也因之成为西藏地方最为强盛的一个教派,而且是“政教合一”的地方势力。萨班不但有“学富五明”的崇高声誉,还兼掌后藏政、教大权。因此,一二三九年,阔端的一名大将多达那波攻打西藏时,将此情况了解并饋给了阔端:“现今藏土,……萨迦.班智达学富五明,请我主设法迎致之(1)。”阔端正需要这样一位人物来达到将来对西藏管理统治的目的,便毫不犹豫地接受多达那波的建议,於一二四四年向萨班发出邀请昭书,邀其来凉州会谈。
(1)牙含章编著《达赖喇嘛传》,第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萨班接到邀请书后,在广泛听取和徵求西藏各层人士的意见后,本著民族统一和为西藏前途著想的强烈责任心,决定接受邀请。当时萨迦.班智达业已六十三岁,携其侄子八思巴(当时仅十一岁)与另一侄子恰那多吉(当时仅七岁)於一二四四年前往凉州,一二四六年萨班抵达凉州。一二四七年初,阔端与萨班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会谈按双方各自的意愿,取得了十分圆满的结果。会谈的重大成就是就西藏归属蒙古问题达成一致协议,并由萨迦班亲自写成一封致西藏各地僧俗首领的公开信,即《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协议内容包括蒙古汗国对西藏的主权关系、户口登记、徵收赋税、地方官史的任用等。
阔端邀请萨迦班至凉州会谈,一是为了西藏的归属问题,另有一个目的是请其在凉州弘法。萨班在凉州“为阔端王及部属授与喜金刚的灌顶,显示种种神通,得到王的敬信”(1)。并“亲授王《大乘发心经》、《大悲空智金刚灌顶》等经,使蒙古国之人成就供养之德,弃绝不善业道,皈依佛教宝法”(2)阔端对萨班的学识很赏识,十分推崇萨班,在凉州城外为其兴建府邸,并将东部幻化寺维修供其居住。
凉州会谈结束后,萨迦寺会派人请求萨班返藏,但萨班认为在凉州更益於弘扬佛法,故决定留驻凉州。萨班在<致蕃人书>中言:“此菩萨汗王(指阔端)对佛教教法,尤其对三宝十分崇敬,以良善之法度护持臣下,对我之关怀更胜於他人。会对我云:“汝可安心说法,汝之所需,吾俱可供给。汝作善心知之,吾之所为善否天知之。”彼对八思巴兄弟尤为喜爱(3)。”从其中可以看出,阔端对萨班弘扬佛法十分支持。阔端自己“曾多次向法王请教大乘之发心等博大精深之教法,僧众对法王亦非常拥戴”(4)。一二五一年,萨班示寂於凉州。阔端为其在幻化寺建灵骨塔,并由其弟子八思巴主持开光安神仪规。
元世祖忽必烈对八思巴更是推崇备至。一二五三年,元世祖忽必烈邀请八思巴至大都,并於一二五六年封为其为国师。一二六四年,元设总制院(一二八八年改为宣政院),以掌管全国佛教及吐蕃地区事务。元世祖赐予八思巴象徵著权力的玉印、金册,领总制院事,因而就使得八思巴在名义上成为掌管全国藏区政教事务的最高官员。一二七0年,八思巴又晋升为大元帝师,“统领诸国释教”(5),“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於西土”(6)从此帝师制确立,元代每一帝都封有帝师。旋又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西藏十三万户地方的税赋,完全赏给萨迦法王收取,作为“供养”。
元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八思巴逝世,忽必烈对他做了极高的评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7)。”元英宗至治年间,特诏郡县建庙通祀八思巴,元泰定帝泰定元年(一三二四),又以八思巴绘像十一,颁各行省,为之塑像。元代帝王对藏传佛教采取的这些政策,无疑促进了元代藏传佛教的发展。
(1)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钓等译《安多政教史》,第二六页,甘肃民族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四月。(下引《安多政教史》仅写书名、页码)
(2)蒙文史藉《胜教宝灯》,转引自魏文斌、李明华《武威白塔寺调查与研究》,载《敦煌研究》,第一0九页,一九九九年第二期。
(3)录自《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第四一页,西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4)周润年译注《萨迦世系谱.法王贡噶坚赞生平》(下),载《西藏研究》,第八三页,一九九0年第二期。
(5)《元史.世祖纪》。
(6)(7)《元史.释老传》。
此外,在十四世纪中叶,元西宁王速来弦蛮坐镇敦煌,崇尚佛教,一三四八年他在敦煌莫高窟刻<六字真言碑>,还出资重修皇庆寺(即今莫高窟第六十一窟)。元太子喃答失於泰定三年(一三二六),重修了肃州城西南三十里山峡内的文殊寺(1)。
明代治者为了“化愚俗,弭边患”(2),对藏传佛教也采取了支持政策,这首先表现在优待礼遇藏族僧人方面。“明代西疆止酒泉”,为了巩固边疆,明朝统治者对河西地区的佛教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明成祖永乐六年(一四0八),西域土鲁番“番僧清来率徒法泉等朝贡。天子欲令化导番俗,即授为灌顶慈慧圆智普通国师,徒七人并为土鲁番僧纲司官,赐赍甚厚。由是其徒来者不绝,贡名马、海青及他物。天子亦数遣官奖劳之”(3)。
明宣宗宣德间重修了张掖大佛寺,其在<敕赐宝觉寺碑>中对佛教导民化俗的作用给予了极高评价,其文曰:“大觉师之道,充周而不穷,神妙而不见,感之而随应,古今所传,彰彰盛矣。其法肇自乾竺,以达震旦,所历之地,人之归向,化之感孚,显著尤多。”并认为其朝“国强民富”,是“佛之慈荫所被及”,故“感荷之诚,晨昏靡间,崇奖祗奉,弗懈益虔。凡所在禅刹,举废修弊,咸致其勤”,而甘州为“故泉之地,居中国西鄙,佛法所以入中国者也。
张掖大佛寺,乃“西来所历之地,佛祖遗化之所,而可后者乎?乃一新其殿宇,而特赐名曰‘宝觉’”(4)。正统十年(一四四五),由明英宗朱祁镇敕书颁赐给张掖大佛寺一部《大明三藏圣教北藏》,於永乐庚子(一四二0)在北京雕版印刷,共计六三六函,六三六一卷,采用千字文编号。经卷分六大部分,集佛教经、律、论之大成。内容涉猎广泛,种类繁多,其中明永乐十八年(一四二0)印制的一0八卷,明正统五年(一四四0)印制的五七九五卷。
此外,还有明正统六年(一四四一)镇守陕甘御马监太监尚宝太监鲁安公王贵,奉敕命组织众多书画名流,用泥金书写的五五八卷《大般若波罗密从经》、《涅盘经》、《大唐西域记》等经卷(5)。这批古本藏经是在张掖大佛寺土塔塔院楼洞里发现的,是国内保存较完整的一部明代佛教经卷。所有这些无疑对河西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宪宗成化年间还敕修了武威海藏寺,并降敕护持,其敕曰:“皇帝敕谕,官员军民诸色人等,朕惟佛氏之教,其来已远,其教本空寂,而以普度为心,故能化导善类,觉悟群迷,上以阴翊皇度,下以利泽生民,功德所及,无间幽显。凉州城北旧有寺一所,岁久废弛,今分守都知监太监张睿,募缘备赀,重新修盖已完,田莊水磨,恐后被人作践,搅扰侵占,具奏乞名,及请给箚僧人道昺义坚住持,并降护敕,兹特允奏。赐额曰清化。仍降敕护持,之后,官员军民诸色人等,毋得於本寺侮慢欺凌,亵渎毁坏,以阻其教,敢有不遵朕命者,论之以法,钦哉。故谕(6)。”这充分体现了宪皇帝利用皇权的力量来支持佛教的发展,巩固其封建统治。
(1)详见《陇右金石录》卷五〈重修文殊寺碑〉。
(2)《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传〉三。
(3)《明史》卷三二九〈西域传〉一。
(4)乾隆《甘州府志》卷十三〈艺文上〉之〈敕赐宝觉寺碑记〉。
(5)张掖地区地方史志学会编《张掖地情业书》第三辑《张掖文物古迹荟萃》,第一六五~一六六页。
(6)《凉州府志备考》(清.张澍辑录,周朋飞、段宪文点校,三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八月,下引同)艺文卷十之<成化御敕修海藏寺碑>,此碑立於成化二十二年(一四八六)。
宪宗还在成化年间敕赐重修了位於凉州城西莲花山上的善应寺(1)。除宪宗皇帝敕修佛寺外,明代还在河西敕建有二所寺院:一是明成祖永乐年间敕建的位於凉州城东北隅的清应禅寺(2),一是明世宗嘉靖年间敕建的位於肃州城西南隅的大赫寺(3)。明帝对佛教寺院常赐敕护持,间或颁赐寺额。例如:明成祖永乐九年(一四一一)敕赐甘州城西南隅的大佛寺额曰“宝觉寺”(4);永乐十四年(一四一六)甘州城南一百三十里的马蹄寺被赐“普观寺”(5);明宣宗宣德二年(一四二七年)赐位於山丹城南六十里的马喝喇寺以敕谕,加次护持(6);同年,敕赐马蹄寺田地山埸(7);宣德五年(一四三0)还赐凉州白塔寺额曰“莊严寺”(8);宣德间赐位於甘州城西南隅的木塔寺额曰“万寿寺”(9);建於明英宗正统年间的东乐隆教寺,“名由敕赐”(10);正统年间敕赐位於山丹城西十里许的大佛寺额曰“土佛寺”(11);正统五年(一四四0),明英宗敕赐位於肃州城鼓楼西的大寺额曰“吉祥寺”(12)等等。得到敕赐的上述寺院,有皇权为其保驾护航,在河西佛教舞台上发挥著重要作用,这是勿庸置疑的。
清代统治者继承了明代对西北的宗教政策,继续对藏传佛教进行护持、尊崇。乾隆帝在其所著《喇嘛说》里讲的很清楚:“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指达赖、班禅),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13)。”清代皇帝继续在河西建寺,颁赐寺额,降敕护持。雍正十年(一七三二),清世祖在肃州柳沟卫(治所为布隆吉)城外西北隅敕建永宁寺(14);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敕赐甘州城西南隅的大佛寺额曰“宏仁寺”(15);康熙四十七年(一七0八)敕赐甘州城南一百三十里的马蹄寺“青莲筏”三字匾额,金镶紫檀塔一座(16)。
上行下效,元明清地方统治者也积极支持河西佛教的发展。在元明清时期,河西的大部分佛寺进行过多次重修,倡导重修并筹措资金的大多是地方官员及巡边太监等(详见后文)。佛寺的建修为佛教徒及其信众提供了活动场所,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总之,在元明清时期,统治阶级为了“化愚俗,弭边患”,巩固其封建统治,遂大力提倡佛教,促进了河西地区佛教的发展。
(1)乾隆《武威县志·建置志·寺观》。
(2)《凉州府志备考》艺文卷十之<敕赐清应禅寺碑记>。
(3)光绪《肃州新志稿·营建·寺院》。
(4)(5)(10)乾隆《甘州府志》卷五<营建.坛庙附寺观>。
(6)乾隆《甘州府志》卷十三<艺文上>之<建马喝喇寺碑记>。
(7)民国《东乐县志》卷四<艺文>之<马蹄山佛殿碑记>。
(8)<重修凉州白塔记碑>,此碑现存武威白塔寺内。
(9)乾隆《甘州府志》卷十四<艺文中>之<重修万寿寺碑记>。
(11)乾隆《甘州府志》卷十三<艺文上>之<重修土佛寺碑记>。
(12)乾隆《重修肃州新志》肃州第五册《祠庙》。
(13)转引自牙含章编著《达赖喇嘛传》,第三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14)乾隆《重修肃州新志》肃州第五册《祠庙》。
(15)(16)乾隆《甘州府志》卷五<营建·坛庙附寺观>。
第一节 凉州
凉州,即今武威地区,元设永昌路,辖今永昌、民勤、武威、古浪、天祝、永登、皋兰、景泰。明设永昌卫(永昌)、凉州卫(武威)、镇番卫(民勤)、庄浪卫(永登)、古浪守御千户所。清设凉州府,辖武威、镇番、永昌、古浪、平番等五县,号称五凉。
一、凉州州治武威
据前文所述,西凉王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结束后,阔端积极支持萨班在凉州弘法。萨班从一二四四年到凉州至一二五一年圆寂,在凉州住了七年,积极弘扬佛法。萨班在讲经说法时,有四各翻译把他的话分成蒙古语、畏兀儿语、汉语和当地的安多藏语,从而使“既不同语言,又不同信奉佛教之徒众亦信仰了佛教,信奉者们皆入大乘教。”
总之,法王使无数僧徒成熟解脱,佛教日益繁荣昌盛”(注释: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着,陈庆英译《汉藏史集》,第二0一页,西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这说明萨班在凉州的弘法有力地足进了藏传佛教的发展。萨班时代,不仅使其居住的东部幻化寺成为一座规模宏大,为凉州诸寺之首的藏传佛教萨迦派寺院,而且还对其他寺院进行加持,多有兴建或扩建,重要的有南部灌顶寺(汉语称为金塔寺)、西山莲花寺和北部海藏寺,这三寺与幻化寺(即白塔寺)合称为凉州四大佛寺(注释:布西码放毫哇德思尔着《凉州佛寺志》,旺谦端智译。),成为凉州藏传佛教发展的中心。
白塔寺 位于武威东南四十里,因原寺院建有一座萨班灵骨塔,塔身外表涂抹白灰,俗称“白塔”,寺因塔名,又因原寺有塔林,传有一0八座塔,又称“百塔寺”。萨班曾在此居住、弘法。萨班圆寂后,阔端为萨班修建了舍利灵骨塔,并在塔内装藏佛经。《安多政教史》载:“修建了一座装有一位阿罗汉和一位菩萨的灵骨和舍利,其它舍利十颗,用金银和墨水书写的许多份陀罗尼咒、许多经书的章节及十万泥塑小佛像等为内藏,仿噶当佛塔形式高十六寻的灵骨塔(注释:《安多政教史》,第一四0页。)。”八思巴时期,“这座萨迦寺院有比丘千余名,大经殿背面的佛塔内装有贵重的十万小泥佛像” (注释:《安多政教史》,第一四0页。)由于白塔寺所处的特殊地位,白塔寺在元代一直兴盛不衰。元末白塔寺遭兵火毁坏,仅存瓦砾。
明宣德四年(一四二九)“西僧妙善通慧国师锁南监参因过于寺,悯其无存,乃募缘重修寺塔,请命于朝,赐寺名曰庄严。宣德五年六月,塔先成,所费甚重,肃王殿不捐泥黄金,特命锁南监参等缮写《大般若经》一部,凡一十四函,计三百卷,不月而成。施无量,仍造小塔十万,实于大塔之心,及钦镇甘肃太监王安、平羌将军都督刘广、都指挥吴升及诸檀善等,由是书志于塔中。”(注释:<重修凉州白塔记碑>,此碑现存武威白塔寺内。)。宣德六年(一四三一),肃王府内臣黄潮宗、藏僧锁南监参又于白塔寺内建菩提宝塔一座,并称此举“专为祝延圣寿,肃王千秋,更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祚绵长,边疆宁谧,军民乐业,四恩普报,三有均资,法界有情,同圆种智者”(注释:<建塔记碑>,此碑现存于武威白塔寺内。)。宣德年间二通重修白塔寺碑中所记的锁南监参,很有学识,先在凉州广善寺(即大佛寺,又称天梯山石窟)任住持,获“妙善通慧国师”封号(注释:参见现藏甘肃省博物馆明正统十三年(一四四八)立脚点 <重修凉州广善寺碑铭>。),后因修白塔寺,任白塔寺住持,对白塔的重新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清代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又对白塔寺进行了重修。从以上记载可知,在元明清三代,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支持,白塔寺一直兴盛不衰,在凉州佛教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海藏寺 在凉州城北五里处,据《安多政教史》载“萨迦·班智达在此处曾讲经说法,大转法轮,并收服了使蒙古阔端汗患龙病的龙魔,该寺有称为当时的圣地之门具有加持力的水井一处。主要的依止处有灵验的佛塔、三世佛、近侍佛子、金刚持、大日如来、无量寿佛、十六尊者等像。院中墙壁上画有各种佛像,有供奉大威德和许多护法神的依怙殿,汉地版的《甘珠尔》大藏经”(注释:《安多政教史》,第一三九页。)。后废弃,时成化十九年至二十三年(一四八三~一四八七)又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重修。据<钱进张太监重修海藏寺碑记>(注释:《凉州府志备考》艺文卷十。)载,此次重修,“进深七十六丈五尺,面阔五十二丈,四面周以垣墙。建山门一间,耳房间各以三,初则天王殿三间,东西钟鼓二楼翼然相峙。廊房间各以九,中则重檐殿七间,殿后到座观音钻檐挟山卷蓬一间,殿之前轮藏三檐,东西祖师伽蓝二殿巍然相向。廊房各七,碑亭各一,后殿五间,功德、护法二殿分列东西。廊房之间各以八,法堂五间,东西方丈间各十二,厢房各五。又其后筑方台高三丈,阔一十四丈,进深十三丈,上建重檐真武殿五间,前龙虎殿三间,左右梓漳灵官二殿各六间,东西角钟鼓楼二座,周围廊房二十三间。台下禅堂房各五间,垣墙外之东南建龙王庙三间,殿前钻檐挟山卷蓬一间,东西廊房各三。立庄三所:一则寺东,有屋三间,水磨房五间,田一顷五十亩;一则东南,有屋六间,水磨房五间,田地十亩;其西北庄一所,有屋三间,田地计二顷焉。凡神佛之尊卑口之大小,靡不具备,丹漆黝垩,金碧辉煌”。这次重修,使原来的藏传佛教寺院改成为汉传佛教寺院,成为时清时期凉州一重要汉传佛教寺院,促进了汉传佛教的发展。
莲花寺 在凉州城西三十里处,《安多政教史》载,“寺内供着一人身量高的黑忿怒明王青铜像,并有像释迦宫城尊行相的称为索巴让摩的遗体。……其它佛殿里供着三世佛、弥勒佛、八尊近侍佛子、大威德、胜乐、喜金刚、大轮、依怙主、护法五天王、观世音菩萨、无量寿佛的报身与化身、度母等;还有许多汉族供奉的神道。第五世达赖喇嘛指出这儿是萨迦·班智达广授显宗佛法的地点。后山嘴上有大佛塔,据说是索巴让摩圆寂的地点,也是班神授灌顶时取净瓶水与彩粉的地方。……该处有供奉慈尊弥勒佛及其眷属,释迦及二胜的两处佛殿”。(注释:《安多政教史》,第一三八~一三九页。)
金塔寺 凉州城西南三十里,《安多政教史》载:“金塔寺即围腰带的洛·昂德王的墓地。据一古记载,众生怙主八思巴给金腰带王授与了大权顶。有人认为按此说法,似乎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墓地。寺庙正中的释迦佛像是萨迦·班智达所修建。……宝账怙主像内装有觉巴师占赛纳保的禅带、头发以及尊者的经卷等并加以禳解。还有当时向国王及随从灌顶用的四方形曼荼罗石台(对于这次的灌顶,众说不一)。此外有众生怙主八思巴修造的三世诸佛、近持佛子等像。其它佛殿里供着萨迦·班智达、金刚持、无量寿佛、宝账怙主、四臂怙主等佛像及大慈法王像(注释:《安多政教史》,第一三八页。)”
除凉州四大寺外,《安多政教史》记载凉州附近有许多藏传佛教寺院,主要有大佛寺、庆平寺、白莲寺、相排寺、参旁洞、图吾寺、庄严寺、黄华寺、弥陀寺、金刚亥母寺、珠巴寺、宝顶寺、东日寺、青英寺、德英寺、霍家寺、万果寺、东坡寺、白莫寺、徐波寺、多塔寺等二十一座(注释:详见《安多政教史》,第一三五~一四三页。)。这些藏传佛教寺院,主要是藏、蒙等族的僧俗进行佛事活动的场所。
凉州地区的传统佛教在元明清时期也有所发展,当时的信众对不少寺院都有建修之举。尽管当时人传统佛教发展衰微,但这些汉寺无疑对传统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凉州重修的佛寺,有碑记记载的主要有以下几处:
大云寺 位于凉州城东北隅,有塔,晋张天锡建(注释:干隆《武威县志·建置志·寺观》。),元末因战乱被毁,明代进行过多次重修,据<增修大云寺碑记>(注释:《凉州府志备考》艺文卷十。)载:“元末兵燹以后重为鼎新,爰复古迹。自皇明洪武十六年(一三八三)始,其募主则日本沙门志满也,未有纪者。旧有浮图五级,未及合尖,至万历壬辰岁(一五九二),本城副将鲁光祖砖瓦砌补,完前功。百八十尺,与清应寺塔双峰插天,称五凉一奇观云。”后本镇总兵达云于塔台前面并建元帝庙一座,“但台下正殿孤悬,左右敞阔无制,非增建廊庑,无以肃内外而壮观瞻。谈者指画如式,卒无有肩其任者,以功程繁灏,所需良不赀也。署印比丘信环倡议修举,于正殿东西建廊房二十四楹,补移对面罗汉殿三楹,伽蓝殿三楹,金装丹垩,岿然焕然,山门角门,增设如制。又以释迦之祖修、磨练及赫灵显异之迹历历图绘于廊壁间,粲云霞而耀日星,俾观干见像会心,恍若亲炙,垂教不显且切哉。材木、砖石、工匠之费,十万所不给者,损赀接济,七越岁而工始成。本就参戎达奇策,前总兵公冢嗣,而此时之檀越也。”这次重修,虽因资金短缺而耗时七年多,但经过此次重修,大云寺形成了一定规模,在凉州佛教中发挥着其重要作用。
清应寺 位于大云寺西,有塔名姑洗,相传周敬王时阿育王所建之一(注释:干隆《武威县志·建置志·志观》。)。此寺在明清时期经过多次重修。据<赖赐清应禅寺碑记>(注释:《凉州府志备考》艺文卷十。)载:“其城(凉州城)这东北隅,旧有北斗宫遗址,相传始终至止时,兵火残燹。永乐间敕为清应禅寺,殿宇巍峨,廊楹绘绚,世称古刹,迄今二百有余祀,肠雨喧湿,瓦毁栋桡,像貌倾颓,殊非所以隆具瞻也。嘉靖辛酉(一五八三六),金台吴公添寿,厥后光山王公光祖来莅兹土,目击心恻,各捐金置树植之具。隆庆三亚贾公仁元又增补天王殿三楹,钟鼓楼各一,主司晨昏,缘工程颇巨,修葺虽饰,尚未乐成。今余(即分守西宁道兼督理粮储屯田水利陕西等处承宣布政司右参议曲梁袁宏德)奉简命,仕优曾憩息于中,常住比丘舌罄巅末,因请命于今中丞三河曹公子登,中丞公许给以帑藏之羡者,遂纠工求木,用续诸大夫之美,于是轮换堂构,烂然称一新也。寺前山门一座,次乃增补天王殿钟鼓楼也,又次即北斗宫故址,东西楹各列罗汉于内。公两隅左祠祖师,右祠伽蓝,中为正殿画廊各一十有一间,毕释迦牟尼脱苦海,登彼岸,参通本来面目,所谓西方圣人者是也。后分两殿,一名弥陀,一名地藏。中道扁曰‘梵王官’,直抵姑洗塔,而禅堂、僧舍环统联络于左右,一每位于元武而万壑潴焉,乐期成也,敞庄严之胜概,壮保障之奇观,甲西凉这雄镇也。”
经过明代几次建、修,其焕然一新。清代康熙年间,又两次重修清应寺塔。据<孙思克重修清应寺塔记>载,康熙乙巳(一六六五)岁仲春,孙思克与刘耀薇诣清应寺,见其前后殿宇并两廊庑暨塔院多摧颓倾圮,乃“首捐俸资,命工鸠材、殿宇重修,惟是塔院尚未修葺。余因会商参议朱公,复捐资作首创,一时营卫文武属有同心,阖城善信均修檀行,爰是拆其颓败之塔院数楹,周围缭以垣墙,使塔身清洁明显,于首层加以栋脊,俾塔隅八角玲玲轩昂,中间复施丹垩,华彩鲜明,梵宫重门,以次修葺。于塔上另制灯砖二百块,塔灯二百碗,盖前此点灯,类用石庄,塞上高风往往吹落,击坏塔身,今而后得此番修制而塔院与正殿山门前后表里洞达,游者改观矣。”
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0)又对清应寺塔顶进行了重修,据<李如荫重修清应寺塔顶碑记>(注释:《凉州府志备考》艺文卷十一。)载,此次重修,“补残葺缺,换旧更新。……是其廊楹绘彩,肆外闳中,金像庄严,烂星丽日”。清应寺及其姑洗塔经过明清多次修缮,成为远所闻名的一处禅刹,吸引了大量的善男信女来烧香拜佛,在凉州佛教舞台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罗什寺 位于凉州城北街,有塔,姚兴时鸠摩罗什建,相传罗什舍利子塔内(注释:干隆《武威县志·建置志·寺观》。)。明清时期,多次修葺,据<罗什寺碑>(注释:《凉州府志备考》艺文卷十一。)载:“塔(罗什舍利塔)光倒影,屡显奇异,历代相沿,兴替不一。明永乐七年(一四0九),有住持僧石宏重修;逮正统年间,则颁赐藏经全部;于隆庆年间,有河湟上人,俗姓以马,讳法林,重修经阁,又于天启重修殿宇。上人年九年十乃涅盘,口放白毫光而始寂灭。后蒙甘肃大都督孙思克、总镇王公用予、柯公彩入阖郡信士等屡加补葺,而定蜀元戎李公子孙亦相赀材,供勷善举。”
以上汉寺经过明清时期的多次修缮,面貌焕然一新,足进了传统佛教的发展。
另外,除上面所举之外,在元明清时期,凉州还有不少佛教寺院,这些寺院有的现在已无遗存,但在当时皆为凉州较为重要的寺院。兹据干隆《武威县志·建置志·寺观》列表如下:
根据以上所列,凉州州治武威共有六十一处藏、汉传佛教寺院,并有许多寺院,在元明清时期得到多资助修葺。众所周和,佛寺是佛教发展的载体,“粤自汉永平间,金天之教流传中土,历魏、晋、齐、梁、随、唐、宋、元间,寰海之内,邦甸郡邑,莫不有寺以阐善教”(注释:<重建土佛寺碑记>,载干隆《甘州府志》卷十三<艺文上>。)。武威有如此众多的寺院,足见其佛教发展之盛。该地的藏、蒙等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大抵全民信教,汉民也有礼拜藏寺的,这从有的藏寺中供汉神可知。从上列所举几处重修寺院的碑记可知,汉民对修寺造塔是积极响应的,他们所捐的钱物,实际上是用来养家糊口的,但为了做功德,死后免受地狱之苦,他们争相向寺院捐资捐财,这充分说明了佛教在民众中的影响之深,说明了佛教发展的广度和深度。
二、平番县(即今永登县)
平番县的佛教,在连城鲁土司的倡导、支持下,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佛寺林立,僧徒众多,佛事活动频繁,成为凉州地区又一佛中心。
鲁土司,蒙元后裔,元亡归明,被封连城,清仍袭职。依据干隆《平番县志·官师志》载:
掌印土司指挥使鲁风翥,其始祖脱欢,元平章政事,明初率部投诚,安置庄浪西山之连城。二世巩卜矢加,以功升百户。三世什加,以军功升都督同知,赐姓鲁。什加生鉴,鉴以功曜指挥使。自此以后,遂以鲁为姓。以指挥使为世袭职,国初依附,仍其世职。
《平番县志》又载:清干隆年间鲁土司辖民“有土民三二四五户,二一六八六人”,“番民四五三户,二三五六人”,共辖民三六九八户,二四0五一人,约等于当时平番县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六·八。
鲁土司为了维护其显赫的政治、经济地位,牢牢地控制着寺院,成为河西地区政教合一的典范。
凉州地区藏传佛教盛行,并发展为一股强大的势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鲁土司家族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必然要借助于宗教的力量,收揽人心。于是他们立寺、建塔,广作佛事,希图利用宗教的神灵,来为土司家族世代承袭的特权服务。其中最甚者,莫过于控制寺院,将自己家族的世袭渗入寺院住持的传授中去。
鲁土司曾建有多处寺院,每寺有大喇嘛一人,即是庙主,多以土司子弟担任,有很大权势。寺内的囊谦,即大喇罚的公所,下面是二喇嘛、三喇嘛,分别司财政和经典,不家众多的普通喇嘛,对民间婚丧疾病等事,祈祝祷诵经。喇嘛按级分职,各住僧房,房内设置锅灶,自炊茶饭,壁上置佛像,悬佛图。喇嘛有终有住庙的,也有半住家半住庙的,因为他们家中同样设有佛堂(注释:赵鹏翥着《连城鲁土司》,第五三页,甘肃人民出版社会一九九四年版。)。鲁土司所建寺院中,最著名的要数妙因寺。
妙因寺 位于鲁土司卫门西邻,系鲁土司之家寺,是鲁土司建立的影响最大、塑像最多、壁画最精的一处寺院,也是鲁土司辖区内的主寺,与东大寺、西大寺、古城寺、嘎达寺、宣化寺、塔尔寺、宗家寺、显教寺等八座寺院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寺院群。《鲁氏世谱》记此寺云:“明宣德二年(一四二七)三月二十二敕谕更名曰妙因寺。”知此寺创建当宣德二年之前。明正统六年(一四四一)对其进行了重修,据<敕赐大通寺碑记>抄件(注释:此抄件现藏于永登鲁土司衙门文物管理所。)载:“庄浪大通河桥驿,乃土佥右军都督鲁公贤之故里也。公之弟剌斡罗祝思自稚年萌善心,早成就,戒行甚谨,而人多敬慕之。比以兹土灾旱相继,遂于所居之旁建寺,以为修禳之所……越一载工完。是以大殿、山门、堂庑、库院、堺墉、垣闼、仓溷、园浯靡不具备……正统壬戌年(一四四二)冬,始请于朝,口赐名为大通寺,具命番僧那尔藏住持,领众焚修之。”
另据《安多政教史》载,鲁土司建造大通寺,并虔诚供奉。经过几代之后,喇嘛洛登巴又扩建了该寺庙,塑造金刚持佛像、法王像等许多塑像及画像,还有从青海瞿昙寺仰来的青铜铸造的三世佛像……以及银针法书写的《甘珠尔》大藏经和朱红书写的《丹珠尔》大藏经等。寺庙后边有两座大佛塔和许多佛像、佛经和佛塔。后在一七二七年,由衮卓仁波且阿旺曲智嘉措做施主,创建了祈愿神变法会,讲授佛法,举行抛掷施食祭,聚有比丘一千五百名,由尊者教授黑帽跳神。此寺院与东大寺(位于妙因寺东)皆由鲁嘉(家)阿阇黎的历世转世化身和鲁土司共同护理。(注释:《安多政教史》,第一二八页。)。
从此段记载,我们可知妙因寺与鲁土司的关系之密切,其“祈愿神变法会”的规模之大。不仅如此,妙因寺在甘青藏区番寺中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明实录》中多次记载妙因寺对明延的朝贡关系,最早着录的是《宪宗实录》卷二二四:
成化十八年(一四八二)二月辛酉,陕西庄浪卫大通寺番僧箚失丹班建寺于本寺东南隅……来朝贡,乞赐名。诏赐东南隅寺曰显教。”
其次,是孝宗、武宗时大通寺番僧屡次来朝入贡和赐宴、赐物的记录:
弘治十五年(一五0二)三月戊子,陕西瞿昙寺都綱尼麻藏卜等、庄浪大通等等……各来贡,赐彩段表里等物有差”(注释:《孝宗实录》卷一八五。)。
弘治十七年(一五0四)十一月壬辰,陕西大通等寺番僧那尔卜等来贡,赐宴并彩缎、衣服等物如例。(注释:《孝宗实录》卷二一八。)
正德二年(一五0七)十二月乙未,大通等寺番僧那尔卜等来朝,贡佛像、驼、马等物。赐宴及彩缎、衣物有差。(注释:《武宗实录》卷三十三。)
正德四年(一五0九)四月甲子……大通等寺番僧那卜等……来贡,赐宴,给赏有差。(注释:《武宗实录》卷四十九。)
正德九年(一五一四)正月己丑,大通寺番僧速南坚藏等……来朝,贡方物。各赐彩缎等物有差。正德九年正月癸巳……大通寺番僧速南坚藏等各来贡,赐宴,给赏如例”。(注释:《武宗实录》卷一0八。)。
正德以后,庄浪大通寺即不见着录,此当与武宗以后,明延对藏传佛教的重视程度日益削弱有一定关系。
以上所记的这种频繁的朝贡关系,充分说明了妙因寺在番寺中的重要地位。因为按明朝的制度,只有法王、国师才有资格向皇上进贡(注释:成化六年(一四0七)有明确规定,见《宪宗实录》卷七十八:“(成化六年四月)乙丑……工部奏:四夷朝贡人数日增,发造衣币赏赍不敷。上命礼部议灭各夷入贡之数,尚书鄒干等具例以闻……斡等以鳥思藏原无定立则例,议请……国师以下不许贡……从之。”),而妙因寺并无封法王、国师者,而这种朝贡关系的存在,说明明朝政府已承认了妙因寺的崇高地位。
清代对妙因寺进行过三次扩建,成为甘青藏区和内蒙古一带颇负盛名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顺治九年(一六五二)五世达赖昂旺·罗桑嘉措、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0)六世班禅罗藏华勒丹伊西来京途中,皆曾驻锡此寺。康熙时,六世达赖仓洋嘉措被统治西藏的蒙古和硕特首领拉藏汗废黜后,在云游途中曾于妙因寺后的宣化寺下榻,得到当地鲁土司的热情相待,他在这里宏扬佛法,被称为达宝佛,故此寺香火一直很盛。妙因寺寺内原设扎仓(学院)两处,分别研习佛教哲学和密宗学科,培养了一批高僧,还曾邀请松巴佛、土观佛、华锐铙布萨等著名学者来此寺讲学,使妙因寺成为连结西藏、内蒙古两地纽约带上的一颗明珠。
除妙因寺外,鲁土司辖寺还有嘎达寺、红城感恩寺、显教孝、宣化寺、塔尔寺及天祝县的东耳廊隆寺、西耳廊隆寺等(注释:详参赵鹏翥着《连城鲁土司》,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鲁土司辖寺的僧众数量也不少,上提妙因寺的“祈愿神变法会”能聚集比丘一千五百名,这说明了妙因寺及其周围寺院的僧众数量是很多的。另外,乾隆《平番县志·建置志寺观》中,还记有东耳廊隆寺,周围住僧五百有余;西耳廊隆寺,周围住僧二百有余,这说明,鲁土司的辖寺是有一定的规模的。
除鲁土司管辖的藏传佛教寺院外,平番县还有数处番寺,乾隆《平番县志·建置志寺观》着录有六处番寺:
从此表也可看出,这些番寺院也是颇有规模的。
平番县还有多处汉寺,乾隆《平番县志·建置志寺观》着录有十二处(注释:本着录有十三处,但有一处即红城堡内的感恩寺为鲁土司辖寺,故此列十二处。)。
综上考察,平番县共有寺院二十六处(注释:实际数量肯定多于此数。),僧徒数千名,以藏传佛教为主,汉传佛教势力衰微,并显现出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与该地的民族构成和封建统治者的宗教政策有关的。
三、镇番、永昌、古浪三县
武威、平番是凉州佛教发展的两大中心,而镇番、永昌、古浪三县所处的地理位置势必会受到武威、平番佛教的影响。
镇番 据道光《镇番县志》卷二《建置·寺观》载,镇番共有八处寺院:
圣容寺 在城内西南,明洪武初年,指挥陈胜创建于城内东北隅。成化五年(一四六九)守备马昭移建今地。嘉靖三十年(一五五一0)重修,崇正二年(一六二九)卢访、李述儒等重修。康熙六年(一六六七)邑人孟良允建观音堂,位于大殿东,偏韦驮殿,背大殿,藏经阁在其后,贮藏经二框,嗣卢敏等改建两廊。圣容寺经过明、清多次重修,在镇番佛教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宝塔寺 在城西关外,明正统年间守备鼓铉千户孟鼎建,顺治甲午(一六五四)邑人何孔述移建城内西街,嘉庆二十四年(一八一九)邑人谢琦、毛建翎、李培简等募化重修。
南塔寺 在南门外,旧名镇远寺,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0)邑人郭维复等募化重修。
迎恩寺 在南门外,道光四年(一八二四)邑人马而诚、孙维本募化重修,添建山门。
地藏寺 在城北隅,明初创建。清康熙三十九年(一七00)邑人孙寿严、李愈桂募化重修。
另有孔雀寺、白衣寺、红岡寺三寺。
从以上记载看,这些寺院都是由明清地方官员、地方绅士创建、重修的,朝延并没有倾心于此,这一方面映了朝延的宗教政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河西地区汉传佛教发展的社会基础。
永昌。据乾隆《永昌县志·建置志·寺观》(注释: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刻本。)载,记昌县共有八处佛寺,见下表:
古浪。据乾隆《古浪县志·建置志·寺观》载,古浪县共有十处佛寺,见下表:
从以上镇番、永昌、古浪三县的佛寺数量来看,远不及武威、平番。众所周所,建修佛寺是做佛教功德的一个重要方面,单从佛寺数量来看,镇番、永昌、古浪三县佛教发展的水平远远落后于武威、平番。这说明,武威、平番凭着其优越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其佛教发展受到中央朝延的青睐,佛教发展甚盛。这充分说明了佛教“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道理。
甘州,即今张掖地区,元设甘州路,治张掖。至元元年(一二六四)置甘州路总管府,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立甘肃等处行中书省于甘州,控制河西诸郡,辖今高台、临泽、张掖、民乐、肃南及青海祁连县部分。明设甘州左卫,治兰(池)县(山丹境)、甘州右卫、甘州中卫、甘州前卫、甘州后卫(此四卫俱在张掖境)、山丹卫(山丹)、镇夷(高台西北)守御千户所,高台守御千户所。清设甘州府,辖张掖、东乐、山丹、抚彝厅。甘州作为河西重镇,元明清统治者对其佛教给予了极大的倾心,其佛教发展甚盛,“兹土僧寮道观,所由遍满城市,施于山谷哉”(注释:干隆《甘州府志》卷十一<人物·仙释>。)!如此众多的佛地,足进了甘州佛教的发展。
一、甘州州治张掖
张掖作为甘州的州治,一直是甘州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寺院林立,名僧众多,为一重要佛教中心。张掖境内有众多少数民族聚居,其藏传佛教也有一定规模。
张掖境内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为马蹄寺。该寺位于张掖城需南一三0里观蹄山,其历史较为久远,早在十六国北凉时期,这里即有许多石窟寺院。明永乐十四年(一四一六)赐名“普观寺”,嘉靖、雍正、光绪年间都会经喇嘛重修,成为喇嘛教的中心。据《安多政教史》记载,明代,甘州提督奉皇帝命令,率十三万大军在此寺迎请三世达赖索南嘉措,足见此寺地位之重要。该寺“以其右侧石岩上有格萨王马蹄的足迹而得名,藏语叫噶丹旦曲林寺。该寺院由琼察格西拉丹修建。他转世的活佛阿旺南嘉任波寺的喇嘛。寺内有大经堂和密宗院”(注释:《安多政教史》,第一四三页。)。担任此寺堪布的都是一些学识精湛、德行高尚的人,所属的溪卡有十四个部落,属民众多。所以马蹄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一处重要的藏传佛教中心。
除马蹄寺外,《安多政教史》还着录有十四处藏传佛教寺院,这些寺院“所属的溪卡有一0五个部落,官人和庶民甚众”(注释:参《安多政教史》,第一四四页。)。由此可知,其经济基础雄厚,为藏传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甘州城张掖,多汉人聚居,汉寺多布在张掖城及其周围。据马可波罗记述,元代的甘州是一个“大城”,城内佛教活动相当活跃,信徒“每月有五日谨守斋戒,不杀生,不食肉,节食甚于他日”。佛教庙宇也很多,“内奉偶像不少,最大者高有十步,余像较小,有木雕者,有泥塑者,有石刻者,制作皆佳,外传以金。诸像周围数像极大,其势似向诸像作礼”(注释:《马可波罗行记》第六十一章,北京高务印书馆一九三六年版。)。据乾隆《甘州府志》记载,甘州州治张掖及附郭共有二十九处寺院,多为汉寺。这些寺院在明清时期多曾得到大规模的建、修,今据乾隆《甘州府志》,对部分佛寺的建、修情况分述如下:
宏仁寺 城西南隅,俗名大寺,一名睡佛寺。据<敕赐宝觉寺碑记>(注释:乾隆《甘州府志》卷十三<艺文上>。)载,西夏永安元年(一0九八)有沙门族姓嵬咩,法名思能建,嵬师归寂后,“刹宇久而愈隆,四远瞻式,巍正常存”。明永乐、宣德、正统年间经过多次重修,至万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近二百年倾颓殆甚”,都督张臣及其子张承允又对“浮图廊庑、千佛阁、大乘殿及轮藏、金刚(一七三四)甘山道岳礼、知甘州府凭祖悦、知张掖县李延桂等又对其进行了重修。宏仁寺以过明、清时期的多次重修,再加上最高统治者的敕赐寺名,此寺在元明清时期的甘州佛教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万寿寺 城西南隅,寺中木塔九层,罗汉五百,俗名木塔寺,北周时期已有之。隋开皇二年重建,唐尉迟恭监修。明、清时期,此寺亦经多次重修,据《重修万寿寺碑记》(注释:乾隆《甘州府志》卷十四通八达<艺文中>。)载,明永乐十六年(一四一八)僧满震“募化兴工,遂大启梵宇”。宣德年间,太监王贵“具疏请颁寺额,丐赐藏经”。清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元旦,提督孙思克“谒万寿寺,目击宝塔剥落,木壁尘封,渐有倾欹之势,于是首倡捐修。四明颜君翼超赞襄不遗余力,工垂成,塔顶放光者久之。顾殿于倾颓,廊庑坍塌,内外俱无完壁,而圣像几归尘土,犹非所以奉金仙而昭虔志也。奚是初诚愈恪谋观厥成遴,遣右营游击韩成等会同善信多人世间庀徒度材,不假麾下一环,不劳民间一夫,而甘场城若官弁若绅士若军民又复踊跃随缘助成胜事,楼殿一新,廊庑改观。五百罗汉尊尊光明,二十诸天在在圆满。卧像显丈六金身,千佛耸百尺高阁。伽蓝护法山门厨库,无一不重加修理。又以僧舍界在院中,南面罗治未免障隔,于是买南邻民人何德新、王承谟、韩士伟地基二,自西至东长十五丈,自南至北阔五丈五尺,亘以墙垣用葺僧宇,而规模始称障碍尽除矣。老僧名彻者,弃儒而译,了悟人也,募众倡功亦有力焉。”经过此次大规模的重修、扩建,万寿寺香火甚盛,成为甘州又一重要汉传佛教寺院。
西来寺 城西南隅,明代建。据<修西来寺碑记>(注释:乾隆《甘州府志》卷十四<艺文中>。)载,西来寺“实普觉静修国师创之于前,其徒刘劳藏喇吉赵呾吧坚错继之于后也。案国师郎法,讳阿札木苏,西土人……从师观目喇嘛游历西藏数载,年益长而愈精佛典。康熙中回中国,遂筑精舍住锡于甘而讽修焉。后朝五台至京师,得觐圣祖仁皇帝于畅春苑之永宁寺,圣祖嘉国师器宇非凡,德品醇厚,特为宠异,赐以普觉静修国师号,赐敕书一,银印一,令统辖甘肃僧众,敷教南山一带黄黑番夷。阅三年,率众贡香马,例以为常。国师念甘郡从古无番藏经,请于朝,奉俞旨准颁红字藏经一百八部,永奠边陲。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国师遂改精舍为寺,建楼五楹,以做贮经之所,朝夕参悟于其中,益窥佛氏微奥,是以道行弥昭,西土归化。国师复发普愿,欲就其趾而宏阔之,以作一方莲社,乃规模粗就,而国师圆定,事亦终止矣。嗣因西彝拒命,王师进巢,平郡王亲统大军,镇奠甘肃。公务之暇,临幸斯寺,概栋宇之后凌替,赐金赐额,令其徙刘劳藏喇吉赵呾吧坚错成就之,以继前志,命名曰西来寺。而绅士有成龙、客民闫海等,皆欢忭出资,共襄厥事,兴工于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0)九月,阅十二载,至雍正十年(一七三四)三月落成,共计大楼十楹,上有弥勒佛像而藏经贮焉,下有宝贝佛像,而国师之真容存焉,其南陪有殿有护国仁王佛像一堂,其北陪殿有护国尊天护法一堂,名极庄严。他如大殿有如来佛像,前过殿山门有大士韦陀天王像……”。从以上记载看,此寺曾行到清最高统治者的垂青,并与中央有进朝贡关系,足见此寺地位之重要,成为甘州又是一处重要喇嘛教寺院。
崇庆寺 城南门外西二里,西夏永安元年(一0九八)建。据<崇庆寺碑记>(注释:乾隆《甘州府志》卷十三<艺文上>。)载,宣德中“居士传觉净辈以起废为已任,化缘城府,缔构殿堂,图复旧观”。明正统四年(一四三九),敕赐“崇庆寺”额。天顺六年至七年(一四六二~一四六三),总兵卫颖“捐金,庀材,鸠工,先作大殿四楹于塔之南,而肖塑三世佛教,撷其幻化之迹于壁;又作天王异殿于前,楹如大殿之数,翼以两庑;蔽以三门,门之内,右为钟楼,碑亭附焉,左为鼓楼,井亭近焉;饭僧有堂,憩客有寮,以及库庾庖湢,凡法所宜有者,莫大备。其栋宇仑奂,像设庄严,芗镫幡盖,鲜洁华好,闻者赞叹,见者欢喜。”
镇风沙塔寺 城南二十里将家村,创始未详。清康熙年间,僧慧涌、慧心等“自捐己资,鸠工庀材,会同檀越闻报国等,增其旧制十之七八,创修佛殿三间,高耸巍峨,势连云汉。中塑释迦佛像,左右供以观音、地藏,前设三教、韦驮,左右耳殿,复塑伽蓝等像,玉质金妆,耀煌耀日。中外各建山门,周围共筑墙垣百丈,穿井坚固,盖欲永垂于后也,自康熙甲戌年(一六九四)兴工,迄乙酉(一七0五)四月落成,改名‘兴善梵刹’”(注释:<重修镇风沙塔寺碑记>,乾隆《甘州府志》卷十四<艺文术>。)。
普门寺城 北门内,始建无考。明成化四年(一四六八)镇守太监严宜世、巡抚徐延章、总兵蒋琬等修。康熙初,靖逆张侯建大悲阁。雍正甲寅(一七三四),提督刘世明、甘山道副使岳礼重修。乾隆丁亥(一七六七),住持文慧建殿三座,增方丈厨房静室。越八载,“塑像装轴,莲花架庄严,花宫璀璨,堂哉皇哉,大普维摩闬闳矣”(注释:<重修普门寺记>载,乾隆《甘州府志》卷十四<艺文中>。)。
除上述院外,甘州府城张掖还有如下寺院,见下表(注释:此表据语隆《甘州府志》卷五<营建·坛庙>。):
从以上佛寺的分布我们可以看出,张掖城及城郭共有近二十处寺院,其余分布在城外山区。张掖城郭分布有如此众多的佛寺,当时佛教的盛况是不难推想的。
张掖除有多处寺院外,还有不少高僧大德为张掖佛教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除上述西来寺僧普觉修国师外,乾隆《甘州府志》卷十一<人物·仙释>还着录有如下僧尼:
班丹臧卜 西域人,居甘,从觉喇嘛受秘密戒行,谨守戒律,道行日彰。(明)太宗朝,赐号“灌顶静觉宏济大国师”,予金印,入观赐齎甚厚,帝亲制偈赞以宠异之。
满震 字雪山,秦僧。永乐十六年(一四一八)来驻万寿寺,感异瑞,矢愿重修。接隋开皇二年(五八二)壬寅九百八十余所之地胍,有尚宝监王贵及代镇太监刘永诚共为乐助,工成,推作开山之祖。
祭钟 字符如,俗姓张,河州里人。顺治四年(一六四七),其父梦老僧授子名众僧保,因延,九岁舍于南溪寺,为碧云禅师弟子。二十岁后启遍参古刹名座,苦砺身心,得付衣钵,续灵济正宗。康熙甲子(一六八四)至甘,卓锡圆通寺,宏演像教。久倾殿宇,焕然重新。寿八十,忽谓其徒曰:“我将逝矣!”备辞檀越,沐浴焚香,书偈坐化,即葬寺后,建塔。
同法 字卜舟,俗姓麻,平番人。先住泰普宏仁寺,工于书,与甘山道副使岳礼有莫逆之交,修无量寿佛殿。后卓锡普门寺。初,舟传江南报恩寺,南耕师钵,本泰普与当家师性泰,字若雷,协力开山,放戒演法,若雷亦名噪一时云。
慧音 字耳观,俗姓王,镇彝人。初隐西门外古佛寺,亦与甘山道副使岳礼有莫逆之交。慧音曾着有《大梅耳观禅师语录》,岳礼为之作序(注释:其序文详见乾隆《甘州府志》卷十四<艺文中>。)。后为宏仁寺领座,着有《云纵遗集》。
王氏尼 时代总兵王汝金之遗裔,王汝金死于贺锦之难,其祖纲、悯忠祠暨家室俱尽,遗婺一人,不忍失身他族,故居旁募建药王庙,奉香火终其身。
易氏阳慧、阳泰二尼 其祖易宗臣,襄阳人,任甘标左营守备,病故。慧幻字原籍民方旭,泰字张掖民张太,俱未嫁夫亡。慧年二十六、泰年二十四,随父住道德庵,剪发为尼。经今四十二载,龄垂七十,以医自给,时党悯之。
从以上所列的寺院及僧尼来看,明清时期,甘州府治张掖的佛教是颇有规模的。张掖佛教的发展,除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外,张掖地主统治者的崇佛护法也张掖佛教发展的根本保证。如甘山道副使岳礼,尊崇佛教,与高僧人大德素有深交,并倡修多所寺院,这些都推动了张掖佛教的发展。
二、山丹县
据乾隆《甘州府志》卷五<营建·坛庙 >着录,山丹县共有佛寺十七所,成为仅次于州治张掖的又一处佛教中心。这些佛寺,在明清时期多亦得到重修,今据乾隆《甘州府志》,对部分佛寺的建修情况分述如下:
土佛寺 一名大佛寺,城西十里许,明正统六年(一四四一),太监王贵、指挥所杨斌建。据《重建土佛寺碑记》(注释:乾隆《甘州府志》卷十三<艺文上>。)。载:“正统庚申(一四四0),镇守甘肃太宗监王公贵选拔沙门淄流精修其道者智莹,号秀峰,住持是寺。秀峰名族后裔,生质敦朴,知识颖拔,投本空师授戒律,传禅定,焚修无间于寒暑,功行圆觉,都纲沙加舍念重其德,给经符牒,慨感寺宇朴陋,乃请于守备山丹都指挥杨公斌倡导檀松,绪材陶甓,经营修建,肇自正统辛酉(一四四一)春,讫工于壬戌(一四四二)岁暮,殿宇、山门、法堂、廊庑、厨亭落成,都司指挥张公熊庄严绘塑,金碧流光,焕然聿新。”后镇守甘肃太监刘永诚巡边,瞻礼喟叹,归请于朝,赐额“土佛”,更增加了土佛寺之知名度。明万历九年(一五八一)巡抚侯东莱又对土佛寺进行了重修。
云台寺 城南五十里暖泉堡外,明宣德四年(一四二九)僧正宗募建。据<重建云台寺碑记>(注释:乾隆《甘州府志》卷十三<艺文上>。)载:“宣德丙午(一四二六),有僧正宗游访过此,忽睹石记于地坡,细视碑文,乃前汉奉敕所造云寺也。……既而正宗发愿修造,乃率信士及佛僧等,取材于山,陶甓于野,木工画士,无远不来。经始宣德四年(一四二九)之七月,落成于成化七年(一四七一)九月。前殿内塑三世如来,背坐观音大士,左右绘画药师佛、十二神王、炽盛佛、十二星官,后殿正塑释迦世尊、阿难、迦弃、两壁图画诸佛菩萨,左右廊文殊、普化、普贤。以至天王殿、钟楼、山门、斋室、僧舍冈不周备。金壁辉煌,猗猗美盛,于四方瞻仰。祷有应,祈有感,佛法由是日隆,善教众兹日着矣。”从此段记载看,云台寺经过此次重建,形成一定规模,促进了本地佛教的发展。
马喝喇寺 城南六十里寺沟口,明正统六年(一四四一)僧沙迦会募建。据<建马喝喇寺碑记>(注释:乾隆《甘州府志》卷十三<艺文上>。)载:“天顺初年,始自僧沙迦会,发心创建,至洪正间,俱就倾圯,复遇僧智莹秀峰,再造鸿工,敬修殿。后有惠诚僧行最上,缵承前模,援例题请,奉敕赐马喝喇寺也。……修前后正殿,供奉祖师,伽蓝、方丈、厨房悉具,塑像俨然,遂开常住地五十亩以资香火。讵意隆庆之元虏酉,假迎佛以求款贡盘住,纵牧践踏污秽,仅留地基。万历辛已(一五八一)之明年,狡寇背盟东归,在人张文、张世龙目击荒凉,不忍坐视,共发善愿,与住持张演玉募化十方,官士乡耆人等捐资鼎新,恢廊旧业,焕然改观。仍添设两廊、罗汉、天王、钟鼓楼、厨房十三间,周围墙垣筑砌高厚,培植树株,森森畅茂。……兹于烽火之余,重睹奂仑之美,鸠工于万历十九年(一五九一),落成于二十八年(一六00),完葺于三十四年(一六0六),庙貌庄严……。”
广化寺 城南八十里花寨堡,明弘法四年(一四九一)指挥赵誉、僧郭月峰募建。据<建广化寺碑记>(注释:乾隆《甘州府志》卷十三<艺文上>。)载:“……云游藏主道昺,号月峰者,偕徒德慧一至其境,徘徊不舍,谓从乡老愿建刹焉。操守山丹指挥赵公誉、牧祖赵德智积善辈,遂同心协德,募缘鸠工,栉沐雨几十余年,欲成寺而未得。维时钦差镇守凉州副总兵刘公晟、太监张公睿各捐俸廪以助之,十方施舍源流而来,择于是堡之中北坎而离,中构大雄殿三间,两庑、文殊、地藏殿各三间,天王殿、塔殿、山间各三间,伽蓝、护教、钟鼓楼各一间,殿宇巍然,塑像俨然,金碧绚耀焕然。……经始于居化庚寅(一四七0)夏四月,落成于成化丙午(一四八六)秋七月,因众工成故,额之于楣曰广化。”
转轮寺 城南关外,康熙八年(一六六九)游击郑罴、守备向腾蛟等募建,至地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四月工峻,“立转轮殿一座,东西厢房六间,钟、鼓俱全,楼后天王殿三间,观音殿、大佛殿各一座”(注释:<建转轮寺碑记>,乾隆《甘州府志》卷十四<艺文中>,)。
除以上所举寺院外,山丹县还有如下寺院,见下表(注释:此表据乾隆《甘州府志》卷五<营建·坛庙>。):
山丹除分布有众多的佛寺外,还有不少高僧活跃在山丹佛教舞台上,发挥革重要作用,除了上述主持建、修佛寺的高僧外,山丹高僧还有发塔寺院的释炳霞。
释炳霞 清山丹卫人。削发住发塔寺,夙有慧业,博通释藏,工诗善书,当时人士咸礼重之,以为古贯休之流亚也(注释:乾隆《甘州府志》卷十一<人物·仙释>。)。
从以上官、民、僧修建佛寺的热情来看,山丹佛教对民众的影响是很大的。山丹佛教还影响着当地民俗,如据道光《山丹县去》卷九<风俗>载:“丧葬殡前三日,乡党亲友来赙,奠间作佛事。”这些佛事活动,反过来促进了山丹佛教的发展。
三、东乐县与抚彝厅
东乐县,即今民乐县。乾隆《甘州府志》着当东乐县仅有三处佛寺,而据民国《东乐县世》,明清时期东乐有佛寺十四处。这些佛寺在明清时期大多都经过重修,今据民国《东乐县志》,对其建,修情况分述于下:
胜泉寺 在县城东关,建于明永乐十五年(一四一七),明清时期,多次进行重修。据<东乐胜泉寺碑记>(注释:民国《东乐县志》卷四<艺文·碑记>。)载:“敕赐胜泉寺,永乐十五年,百户王敬跟随钦差太监鲁公,前往萨麻儿罕地和番,取讨佛骨。夜梦金身显现,回还就于东乐驿门外盖寺一所,将骨塑在释迦牟尼佛身内,又塑观世音菩萨,彩画五十三参。上以延祝圣寿,下以化导愚庸。户侯王刚同善友王觉秉等于景泰七年(一四五六)重建,至天顺四年(一四六0)十月,内户侯王圯同施主王觉秉等僧人觉忠造铸洪钟一口,法鼓一面,重修伽监、祖师殿二年,钟、鼓楼二座,天王殿一所。”
景会寺 在景会堡,明天顺元年(一四五七)建。明代亦多次重修。据<重建景会寺碑记>(注释:民国防大学《东乐县志》卷四<艺文·碑记>。)载:“……天顺元年(一四五七)僧人河迦舍念因野憩梦惊,发心创立此寺,修建完毕,四年(一四六0)题奏奉,敕赐寺额曰‘景会’,一方善信冈不瞻礼。嘉靖三年(一五二四)甲申,赋匪侵围,焚毁倾颓二十年,辛丑(一五四一),僧罗谷领真,舍念四世孙也,不嗜物欲,不贪瞋痴,僧行重之,庶人重之,虽贤士夫亦重之。允有僧道也,遂捐也百马贸易重修,凡殿宇、门堂、禅房、僧舍俱鼎建焉。然鼎建之功方成,而绚饰之力未备,二十五年(一五四六)两年,领真辈赴京进贡,袭授法缘清净喇嘛职事。京回,殚心竭力,益励前修,逾三十四年(一五五五)乙卯而落成,规制敞大,焕然复新,见者莫大惊惧。僧行善信欢悦皈依,虽番夷之人闻知,亦源源而来,拜礼不绝。”
隆教寺 在南古城,明正统年由马蹄寺旧迹移建。据<重修隆教寺暨厘正田租记>(注释:民国防大学《东乐县志》卷四<艺文·碑记>。)载:“旧迹在马蹄寺前,大明正统间,公、聊、将帅有巡历斯土者,见其身颓废,遂移建于南古城堡。其铜佛三尊、阿罗汉十有八座,谨依位列,备极尊严。前后殿宇有巍峨。固廊连贯,钟楼鼓阁靡不完整而工丽焉。噫,盛矣,诚与马蹄寺相颉顽矣!至寺名系尊敕赐,若谓佛非异域圣人,从等何钦奉若是?且购置虎喇、马蹄、宣城及大募化西渠头二、三坝等处田租,以供香火。迨年远岁更,不独庙貌倾颓,即香火之资亦留遗无几。间有发心修理者,大都因陋就简,不置可否,讵能使原有庙产完全保守,以至于今耶!张公起龙素性好善,自奉简命守是城,即率本堡士庶捐傣助资,悉为鼎新焉。非甚诚切,亦鸟能至此!因追究其香火田租,他渠如故,独二坝一画夜,水为豪强所隐占。公令善姓赵英、孙得祥等往控于掌印,靳公伊复捏诉上台,蒙观察传公奉政,彭公断结,仍命使水者岁出租二石,以归本寺。”通过康熙年间的这次重修暨厘正田租,提高了隆教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为其在有清一代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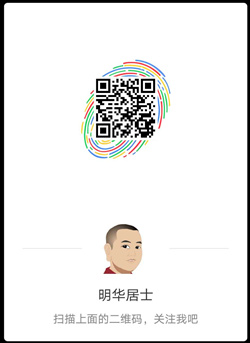
电脑上扫描,手机上长按二维码,进入明华学佛微博,点关注
五明学习: 工巧明: 地理 | 雕塑 | 绘画 | 建筑 | 历史传记 | 农工商业 | 书法 | 天文 | 舞剧 | 哲学 | 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