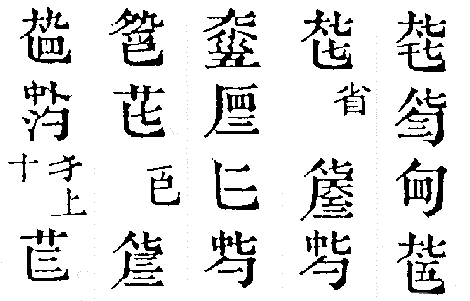|
古琴减字谱的文化哲学 |
|
古琴曲谱在常人看来尤如天书,很有神秘感,那奇异独特的方块字符,很难让人相信是一种乐谱。《红楼梦》中贾宝玉第一次看到琴谱时误以为是天书,被林黛玉嘲笑;《笑傲江湖》中洛阳金刀王家将琴谱当作《辟邪剑谱》,造就了前往绿竹翁处辨认曲谱而使令狐冲识得任大小姐学琴以至最后的琴箫合奏“笑傲江湖之曲”的美满姻缘。就像对任何事物一样,往往当我们不明其事理时才会有神秘之感,在人类的词典里“神秘”几乎就是“未知”和“无知”的同义词。就好象习惯了拼音文字的西方人初看中国的方块汉字感到很神秘,以为很难学一样,习惯了汉字的我们在看那似字非字的古琴谱字时,也感到很神秘,并自然感到很难学习了。甚至有弹琴多年,只从老师那儿学习弹奏方法,因为畏难情绪,一直不愿去学习琴谱的。
减字谱是由最早的文字谱发展而来的,却已与忠实记录演奏方法和过程的文字谱有极大不同,它实际上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将文句记录缩减、精简、组合成一种新形的方块字。与近代的简化字不同,它不是将一个繁体字精简为一个简化字,而是将一段描述左右手弹奏方法、弦序、徽分、音乐处理的文字语句缩减成一个新的字符,而这种缩减却毫不减少这一段文句的信息且比原来的记载更明白,一目了然,便于视奏,按谱循声,由此实现了既不脱离汉文化传统(毋须用新形符号如阿拉伯数字及线条蝌蚪等)又符合了器乐记谱需要的新型乐谱的创造,这种创造在人类的音乐史上是全新的,在世界各种器乐专用谱式中是独一无二的,而这种独一无二并非标新立异,而是符合七弦琴弹奏特点的必然结果。 对古琴减字谱最大的不满是认为文字谱的缺点如“无音高旋律的直觉、不便于记出明确的节奏节拍、篇幅繁冗”等“在减字谱中依然存在”,认为这是一种“缺憾”,是古琴“记谱技法的不完善”,它甚至“影响了琴乐的继承与发展”。但中国古琴千余年来六百多首琴曲、三千多种传谱、两百余部琴谱,正是这种“不完善”的记谱法所记载的,而千余年来的琴乐,也正是在这样的传承中“继承与发展”的。如果说到近代古琴的传承出现危机,问题恐怕不是在减字谱,而是在社会文化的变迁。因此,对减字谱的“缺憾”如何认识,端看我们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取决于我们的观念。如果我们以一般音乐乐谱的标准看古琴减字谱,一种无“音高旋律”、无“节奏节拍”的乐谱无疑是“缺憾”的,甚至根本不够格称得上是一种乐谱,因为它不具备音乐之音高、节奏的最基本要素。但千余年来中国古琴在这种记谱方式中稳定地“传承与发展”的,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奇妙的事。 值得思考的是,历代琴谱中对琴学之律、调、曲、论等有着系统而精深的研究记录,例如关于音律的研究,看看《琴书大全》之卷二,即可知是多么地细致入微,在外行看来近乎繁琐,如坠云里雾里;相对而言,乐谱之“时值”、“节奏”的标注方法应该是较为容易的事,古人难道真的做不到吗?我认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音乐的节奏与速度,在中国传统中称之为“板”或“板眼”。民初琴家杨时百认为“古谱不注板,非不知有板,似不知注板之法”,对此应该存疑。事实上,杨时百注板后的《琴镜》并未被广大琴人所接受,琴人的喜爱的还是以前的琴谱。其原因得超出音乐功能范围,当在中国文化的哲学观念中去寻找。就乐谱的实用功能而言,“注板”(标注了节奏、音高)的曲谱无疑更容易使用,但中国琴人之抚琴,从来就不是为了在乐器上精确地重复出别人的旋律,而是要抒发自己的胸臆、弹出自己的心声来。尤如书法不是写字、绘画不是照相,同一诗句的书法应当各具神韵,同一山水的绘画往往千姿百态,操缦也不是准确地按谱弹出一段音乐旋律,而是要有操缦者自己心灵的音声才对。同中国艺术之书法、绘画重神意气韵而不在“形似”上一样,琴乐也一向是以意境为重不汲汲于节奏之合拍的。严格说来,琴乐本无“拍”,“拍”乃生于心,故板有“心板”之说,而谱也有“心谱”之谓。因为究竟而言,音乐之节奏板眼,发源人类身心血脉的律动,乐句的旋律与人的气息是相应的。琴乐之乐句恰如人类的呼吸意念,往往是自由的、散文诗一般的,也称“散板”。精致地分析会发现琴乐之散板似散而非散、形散而神不散,其中有一种更高级的、更精微的、与人类身心血脉之律动的相应的节拍,故可以规整、也可以不规整,完全是“发于心”、“应于手”而“形于声”也。就记谱而言,古琴之简字谱可以说是“得其妙”了,体现出中国文化自由人文的气息,与中国艺术之根本精神一脉相承,岂一般音乐范畴之乐谱可比?! 故认识古琴谱当从文化哲学的层面,以中国艺术精神来领会才能悟得其妙。或许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崇古、泥古而已,并举出后期琴谱如清代《五知斋》、民国杨时百及最近的《梅庵琴谱》中试图标记拍子时值的努力为证,说明古琴减字谱本身也正在发展,古谱不记节奏实为“缺憾”,乃是一种不完善。若然,我们在原无标点符号乃至句逗也无的佛典道藏和古代诗文上加注句逗乃至近代的引号、冒号、警叹号等,是否就证明了佛典道藏或中华古诗文有所不足、确有“缺憾”,而是靠我们在加以完善、予以发展呢?恐怕不然。应该说,古人毋需句逗即能明了文义,这在那个时代的文化中并不为难。只是时势降而文化异,我们难以直捷明了那个时代的文本,而不得不借助于断句以及种种标点如感叹号等才能明了古人的思想和感情了。从笔者给佛典加标点的经验来看,问题真是多多!清代、民初加注板眼的努力亦然。问题只在于后时代的我们!所以切勿妄自尊大的以为自己在“发展”什么。就像古琴谱一样,相信唐宋时代的琴人若偶获《幽兰》古谱,其打谱会较二十世纪的琴人容易得多,因为相对而言,他更容易把握那个时代的心律。故今人不必因打谱的烦恼而怨怼古人,古谱本不为今人而写。若我们真正好古、孜孜于古音,还是去追寻那个时代的文化、体验那一种精神、领悟那一种心律吧,去努力成为一个《神奇秘谱》所说的“达者”吧! 再从古谱功能而言,也有异于今日一般音乐乐谱,若以今日之标准来要求减字谱,当然会觉得古谱有缺了。古琴减字谱在古代七弦琴“口传心授”的传承环境中主要起着“备忘”的作用,非同今日之乐谱,要求照之演奏即能重复出音乐旋律来。古代琴乐之传续,其节奏和神韵既有赖于老师的“口传心授”,也有赖于琴弟子自身的修养领悟,故一切不必“固化”于琴谱,如前所述,也不宜固化于琴谱。若琴乐真正固化了,将节奏时值完全确定,则如《神奇秘谱》中所言:“使其同则鄙也”,就落于下乘了。古人操琴的理念不是音乐再现,而是“各出于天性,不同于彼类”,以“其涵养自得之志见乎徽轸,发乎遐趣,诉于神明,合于道妙,以快己之志也。岂肯蹈袭前人之败兴而写己之志乎?”(《神奇秘谱•序》)今人之传谱,借现代传媒而广传,某些曲操几乎千人一面、精巧“仿真”,确实听之令人“败兴”,此琴乐之衰象也。 《神奇秘谱》还道出了减字谱不标节拍时值的另一原因,在今天我们或许会判为“封建”“糟粕”者,其谓:“……太古之操,昔人不传之秘,故无点句,达者自得之。是以琴道之来,传曲不传谱,传谱不传句。……是琴不妄传以示非人故也。” 可见古人于减字谱实非如杨时百及今天的我们所以为的“不知注板之法也”,而确实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其中“琴不妄传以示非人”对学琴者文化与道德素养的要求以及不标点句而令学琴者努力提升自己的学养,成为“达者”而“自悟自得”的教学法,可能不是什么“封建糟粕”、不利于古琴普及和不“为人民服务”的错误观念,而恰恰是符合古琴文化特质、维系古琴不失本位、不降品质、见正而行高的传续方式,是保留优秀民族文化精华的高明方法,应该是更高层面的“为人民服务”吧。 当然,结合今日时代的实际需要,我们完全可以在古谱上作出新的标注,加以节奏符号,但那不是古谱有“缺憾”,而只是今天有需要而已。并且,即使今日有此需要,仍宜明其作用乃在初学之方便,并非古来谱式实有不足而必须改之。上个世纪初一时流行在古减字谱上加注工尺确定音高时值,已有人指出这只是为初学容易成调,作为一种”操缦捷径”;“至于久久习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固不必拘拘于此也。”因为,“琴曲有天然节奏,非如时曲必拘泥板拍,惟在心领神会,操之极熟,则轻重疾徐自能合拍。”(《琴学入门•凡例》)可见古琴减字谱所要求的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今日我们以五线谱、简谱或新创节奏符号来规定琴曲的高下板眼节奏,幸勿忘却此意。再者,这种“琴谱改良”,宜在减字谱的原有模式下合理“发展”,例如《五知斋琴谱》中所用的“长竖粗线”、“短竖细线”等节奏符号,而不宜另创一套符号乃至用阿拉伯数字等另一文化系统的符号来进行“中西医结合”,创造所谓“五线记谱法”等致使琴谱不伦不类。就此而言,西安琴家李明忠先生“以传统谱式的文化模式为本,以借鉴现代谱式的科学成份为用”的思想我十分认同,他为建立一套符合传统模式的节奏时值标注符号所作的尝试十分可贵。李先生的构想看上去不仅仍有古谱之美,而原减字谱之妙仍多半保留着。前几十年的五线谱、简谱与古琴减字谱并排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有其一时的贡献、也有其长远的流弊,如李明忠先生所说的“反主为客、舍本逐末”、“对主体文化的委曲”(《中国琴学》第三章),如丁承运先生所说“西方符号系统传递的有别于传统琴乐节奏规律的信息,对以后琴乐所产生的影响”、“以西洋拍子强扭中国的板眼,中国音乐已失掉太多的弹性节拍”(《世纪古琴艺术的传承与变迁》)等。在今天,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刻反省了。 至于“篇幅冗繁”的问题附带说明一二:传统减字谱是相当精简的,例如《获麟操》之减字谱若用标准4号字排版不足两页,而与五线谱合排竟占据满满4个页码。所以“篇幅冗繁”的恰恰是西洋乐谱而非古琴谱。这与中国汉字是一样的,据说在联合国文件中同样内容的文件,在各国文字中,以汉语文件篇幅最少、重量最轻,此亦一妙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