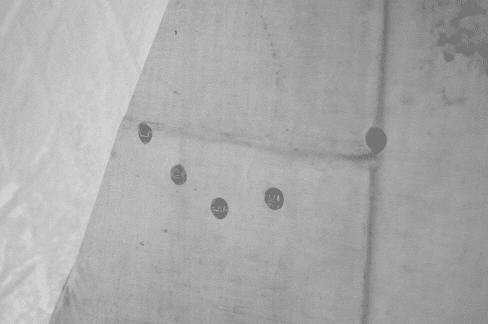|
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一件文物——许广平捐赠给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唐卡 |
|
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一件文物 ——许广平捐赠给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唐卡 作者:夏晓静 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的鲁迅文物中,有许广平1956年捐赠的一幅唐卡。由于它的来源和定名一直未能搞清,所以这件藏品至今没有归类,为了解决这个归属问题,2008年12月23日在我馆召开了这件文物的鉴定会。会上请来了鲁迅文物专家叶淑穗和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专家罗文华研究员,到会的还有周海婴先生、孙毅馆长以及文物资料保管部的人员等。 为了弄清楚这件唐卡的来源,我多次请教了叶淑穗老师,她首先带我查阅了鲁迅文物的原始记录,找到了一本灰色的练习本,叶老师指着本里的字迹说:“这些都是许羡苏的手迹”,许羡苏是许广平的同学、鲁迅文物交给国家后的第一个接收保管者。我仔细翻看了这个本子,发现其中两页上有记录唐卡的信息,一页上写有“冯雪峰长征背回少数民族图”;另一页上写着“冯雪峰长征带回画 连框 1 放故居”,本子最后一页还贴有一张许广平捐赠文物时的记录单,上写着:“(1)太炎遗墨轴 (2)冯雪峰长征画 (3)鲁迅油画 (4)许广平交来木框两个 共五件 于八月卅一日寄于故居 许羡苏”。此外,叶老师还提供了很多重要的信息,她说:许广平在北海大石作胡同居住时,她、杨宇和许羡苏曾多次到许先生家,在交谈中,许先生曾跟他们说:“这是冯雪峰送给鲁迅的。”叶老师还记得许羡苏给她介绍这件文物时说:“这是小叶丹送给冯雪峰的。” 2008年12月29日,叶老师又打电话来,说她又给鲁迅博物馆第一任副馆长,当时负责鲁迅生平陈列展的杨宇打电话询问这件事,88岁高龄的杨宇对她说:“这幅唐卡是冯雪峰从长征途中带回来的,在第一次鲁迅生平陈列展中,为了表现鲁迅和冯雪峰的关系,曾经想把这幅画放到陈列上。”但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和唐卡的内容未能展出。 叶老师还给冯雪峰的儿子冯夏熊打电话询问此事,她说:“夏熊肯定地说,这是冯雪峰从长征途中带回延安的。”1936年4月,跟随中央红军长征一起到达陕北不久的冯雪峰,又接到了中央的命令,以特派员的身份由中央派人护送到和张学良东北军驻防的交界地,与张学良部取得联系,并由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负责将冯雪峰送到南京,最后辗转到上海,住在鲁迅家,当天晚上,冯雪峰就向鲁迅讲述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经过。 1935年5月12日,党中央召开会理会议,决定红军经冕宁进入彝族聚居区,冯雪峰、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李一氓是五个军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所在的编队被称为“上级干部队”。每个人都担当着“政治教员”的职务,负责营、团干部的学习。在艰苦的行军中起到了“党校”和“红大”的作用。亲历长征的冯雪峰曾经三度撰写红军小说,保存了很多“关于长征”的资料,但终因历史原故没能留下,这对他个人、对中国当代文化史、对红军长征史都是件憾事,也使我们的考据工作陷入困境。 许广平先生当年捐赠给这幅唐卡是装在一个栗色的镜框里,镜框的尺寸为84.4厘米×52.5厘米,唐卡的尺寸为50.5厘米×34厘米,唐卡下面衬着的是一张托裱好的浅黄色、带花纹的绫子。鉴定会上,为了鉴定的准确性,我们轻轻地将唐卡从镜框中取出,展示在罗文华研究员面前。他细细地观看着唐卡的每一个部分,然后,让工作人员把它翻过来,他认为,唐卡后面一定有字。果然,画的背面有五个梵文字母,随后,他开始为我们详细讲解了这幅唐卡的绘画内容、艺术风格及创作时间。 这幅唐卡经罗文华研究员鉴定,名为“大成就者冬必巴”,其主要绘画内容是大成就者冬必巴(有的翻译成东毘巴,还有的翻译成宗比巴、甘帝巴、多必巴)和明妃骑着老虎从山林里修行出来的故事。大成就者指古代印度历史上专门修习密法的大师。根据西藏历史传统,大成就者的数量不一,最常见的说法是84位大成就者,冬必巴就是其中的一位。大成就者不仅修行有了成就,而且还把他们修行的体验记录下来。 在藏文本的《八十四大成就者》中,冬必巴排在第四位。他是一个国王,他娶了一个出身首陀罗 (贱族)的女子为妃,臣民们不愿意接受这位明妃,国王毅然决然的放弃王位,和明妃遁入山林修行了。明妃是成就者密法修行的助伴,一般来说,明妃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临时供献的女子,在修行密法的时候,弟子们要供奉一个非常的纯洁、聪明和漂亮女子;还有一种是由上师自己找到的一个女子,既是他的妻子,又是他的明妃。利用明妃作为修行法是藏传佛教后期吸收印度和尼泊尔怛特罗修行仪轨的结果,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藏传佛教中有很多所谓的双身修行的欢喜佛形象。在这里,男女双方分别象征智慧与慈悲的双运、方便(即方法)与智慧的双运、大乐与空的双运等,通过这种双运,可以迅速成就佛果。大乘和小乘佛教都不主张即身成佛,他们认为人要经过艰苦而漫长的修行,积累无数的功德,经过无数次转世轮回才能最终成佛。大成就者就是实践密教即身成佛理论的先行者和理想主义者。 冬必巴腿上搭拉的人皮,象征着他已摆脱了肉体等外界客观的束缚。他骑在老虎背上,身带骨饰,右手握着蛇鞭,左手捧着甘露,怀抱着明妃,表示他的密行已经修行成功。蛇,代表人的贪欲,所以常会在身上装饰蛇,他手上拿着的蛇,说明他已经征服了自己的欲望。 唐卡背后,在冬必巴身体相对位置上有五个梵文字母,与他身体中脉的五个脉轮一一对应。根据藏传佛教瑜伽修行的理论,人体正中部分从下往上,直到头顶共有五个脉轮。五个梵文字母的位置代表五个脉的位置,密宗修行就是要把命气(即生命之气)通过整个中脉各轮,打开脉轮各结,最后通过头顶上的梵穴与所修行的本尊佛像合而为一,顺利达到西方极乐世界或某个佛国世界,达到最后的成就,即不死不灭,无限超越世间轮回,永生永在的佛果。这也就是所说的佛教修行瑜伽,与平常我们作为气功或健身练习的瑜伽有本质的不同。 成佛以后,他的精神就可以不灭,但密教修行的目的不仅在于自利,还有利他的目的。他虽然已经达到超脱的精神世界,但并不意味着他会马上抛弃肉体,抛弃尘世,为了实现他普度众生的伟大理想,他还要借助肉体,继续生活在人间,帮助他人成道,这时候,他的肉体对他来说只是一个交通工具。 冬必巴头顶上方有大持金刚的形象,传统认为,所有的佛教密法通常都是从金刚菩萨演说而传到人间的,金刚菩萨在密教中就化现为本初佛大持金刚。 这件唐卡创作的时间最早可至18世纪晚期,颇有噶玛嘎智派绘画的特点,这种艺术风格在古代康区,即今天四川西部一带最为流行。四川甘孜州德格县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艺术中心。这种风格的绘画与西藏传统绘画有明显的不同。西藏传统绘画以大面积色块平涂,强烈色彩对比为特色,给人以强烈的感官刺激,使观者感受到巨大的心理震憾和威慑,以渲染宗教信仰的力量为目的;而噶玛嘎智派绘画则一改庄严肃穆的宗教气氛的主调,大量引进和采用汉地绘画元素,如此画中的假山、怪石、兰草等,通过晕染的方式表现天空的深邃、山水的远近,将尊神及其背景的景深扩展开来,层次分明,颜色淡雅,画面丰富,增加了更多世俗化的成分,更贴近平民化的审美趣味。这种风格流行于18世纪后期的藏东地区,即金沙江、雅砻江和大渡河流域。在这一地区的许多民族都深受此风格的影响,创作并保存下来一系列的艺术作品。此唐卡当是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一幅。 这幅唐卡采用的大多是植物颜料,与西藏本土主要采用矿物颜料的情况不同。矿物颜料一般涂层较厚,容易结块、剥落,不易保存。此唐卡因受汉地的影响,画师主要采用植物材料作为颜料。 据罗研究员讲,原画还应该有一个镶边,镶边上有天干地支,是后缝上去的,不知为什么拆掉了,可能是镶边很硬,不利于携带,如果带着镶边,无法折叠、无法卷起来,很不容易携带,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把它拆掉了?周海婴先生说:“当时拿来就是这一块,如果带着镶边,父亲是不可能把它拆掉的。” 罗文华研究员最后说:“在藏传佛教文化区,人们之间的交往赠送唐卡的情况并不多见。只有在关系非常好的朋友或上师之间才会赠送唐卡作为礼物。况且此幅唐卡是一幅古代的唐卡,在寺庙或佛堂中,此类唐卡都被视为圣物,一般不会轻易送人。赠送这种唐卡的人一定是对于对方极其尊重的一种表示。再者,赠送大成就者题材唐卡的情况也不多见,朋友间通常以赠送释迦牟尼佛、观音等吉祥慈善类题材的唐卡为主。大成就者通常成组出现,因此,这幅冬必巴唐卡应该是一组大成就者唐卡中的一幅。如果这件东西跟小叶丹有关系的话,应该是小叶丹比较看重的东西,不是随便的礼品,但是像送这个题材的是比较罕见的。” 周海婴先生听说要请专家来帮助鉴定这幅唐卡,他非常高兴和重视,并亲临会场,当他听完专家的鉴定意见后,脸上挂满了喜悦,看看唐卡,又看看装唐卡的镜框,用手轻轻抚摸镜框,最后深情地说:“我家里现在还有这样的框子。” 作为鲁迅的老朋友冯雪峰深知鲁迅酷爱艺术,而且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20世纪30年代,鲁迅大力倡导新兴木刻运动,冯雪峰鼎力支持,将木刻青年林夫与野夫等介绍给鲁迅。鲁迅是冯雪峰“一生中最敬佩”的人之一,这幅唐卡应该是冯雪峰把它当成极其珍贵的艺术品送给鲁迅的。 在红军长征途中,红军总参谋长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结盟,书写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传奇,留下了一段 “彝海情盟”的动人佳话。当时,刘伯承赠送给小叶丹一面红旗,上面写有“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基)支队”, 解放后,小叶丹的妻子将这面保存多年的旗子让驻军领导转交给刘伯承,现存国家博物馆。这面旗子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实践的见证。 但在什么情况下小叶丹将这幅唐卡送给冯雪峰的?这里又有怎样的故事?由于当事人都已离世和资料的匮乏,可能将成为一个永远的谜。可喜的是这件唐卡的定名和到鲁迅博物馆的来源已很明确了,这些都使它具有了双重的文物价值:它既是长征途中少数民族送给红军的礼物,是对少数民族和红军情谊的记忆;同时它又是鲁迅文物,是冯雪峰和鲁迅友情的见证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