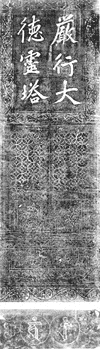|
从朱颜轩冕到云水高僧 大金故慧聚寺严行大德闲公塔铭考 |
|
从朱颜轩冕到云水高僧 大金故慧聚寺严行大德闲公塔铭考 起源于唐代中叶的禅宗,作为佛教的一个派别,发展到宋、辽、金时期,已经成为士大夫的宗教了。当时冠以“居士”之称的“僧化”士大夫,和被赐以官爵的“仕化”禅师充斥朝野,成为一种延续数代的普遍现象。当然其中也不乏更为彻底的“逃禅”者:即弃官入山,落发为僧,布纳蔬食,游锡四方,成为真正的一心向禅者。 从内容上看,《大金故慧聚寺严行大德闲公塔铭》仅是一篇僧人传略,然而,因传主的特殊经历,而使这些叙述文字带有丰富的历史信息,折射出辽末至金初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多方面的史事,正史、补史的作用兼具。对这样一件重要的金石文献,不可不著录,不可不疏证。现就石刻残存的文字,结合辽金史籍,作初步考释,书之于下,祈方家赐正。 一、弱冠登第 由辽入金 塔铭首题“大金故慧聚寺严行大德闲公塔铭并序”,既是石刻的题目,又标明了墓塔葬主的国度、所在的寺院及法号、法名。其中“大金”,为金廷通行书例,是“大金国”的简称。此种书例,屡见于唐、宋以降各个朝代的文书、碑版,与在国号前加“有”、“维”、“皇”、“圣”同义,而加“大”者较多,如“大唐”、“大宋”、“大辽”、“大夏”,以至后来的“大元”等。以塔铭用“大金”,即循唐宋以来石刻文之常例。 “慧聚寺”即今戒台寺,位于北京门头沟区永定镇内马鞍山上。始建于隋代开皇年间(581—600年),原名慧聚寺。该寺自辽、金至元代中期,一直被公认为是北方律宗的中心,因而成为中国佛教的最高授戒寺庙之一①。“严行大德”,应是朝廷在墓主生前赐予他的封号。《大金国志》卷36《浮图》谓:“浮图之教(笔者按:指佛教),虽贵戚望族,多舍男女为僧尼。惟禅多而律少。在京曰国师,师府曰僧录、僧正,列郡曰都纲,县曰维那。披剃威仪,与南宋等。所赐号曰大师,曰大德,并赐紫。”据此可知,“严行大德”乃金朝皇帝赐封给墓主的法号,但究竟在什么时候、是由哪位皇帝所赐,是否一并“赐紫”(即赐穿紫色袈裟)?因为石刻文字的剥蚀,而难以确知了。漆侠在《金代佛教》一文中说:“金代试僧制度大体上承袭辽制,而较为严格。……僧侣的考选规定三年一次,就经、律、论三部门课试,中选的授为三宗法师。这种考选每次以八十人为限,由朝廷指定官员办理。法师中学行优异的,更由朝廷敕加种种名德称号,如佛觉大师、宣秘大师等。”②可知在有金一代,大师或大德称号,不是很容易获得的。另外,首题中的“闲公”,为墓主法号悟闲的一种尊称。古人有别今人,常在名讳后加公或先生称之,以示恭崇。“塔铭”,是一种文体,与墓志、碑文同多 异少,亦可视为一类。多包括志和铭两部分。首题中的“并序”,即是“志”的部分,志多用散文体,叙死者姓名、籍贯、生平,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以示对死者的悼慰。志、铭在古代石刻中,有分用的,也有合用的,而后者较为多见。 此铭志文在前,首先简约的叙述了墓主的籍贯、姓氏和进士及第的过程: “严行大德悟闲,白人,姓张氏,初名伟,字保之。幼失所怙,而宿植善因,蚤(早)慕真谛。十岁,从天庆即伸大师受经业,日数百千言。十七,返亲舍,更读儒书。工辞赋,才誉籍籍,一举中进士第。”
严行大德灵塔局部拓片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地域名称“白”。此地名不载于《金史·地理志》,但见于《辽史·地理志》三中“京大定府”条:“大定县,白故地。以诸国俘户居之。”又,《辽史》卷一一六《国语解》:“奚、,国名。中京地也。”考辽之大定县,为辽中京大定府之倚郭县,辽统和二十五(1007年)置,地址在今内蒙古宁城西。此地金代海陵时期始,置为金北京治所。据《辽史》所记:“诸国俘户居之”可知,此地为五代十国以来中国北方一处多民族聚居之地,俗有“白”之称。另外,“白”也是古族之名,亦称“”,乃铁勒十五部之一,隋唐时居潢水(今西拉木伦河)以北,风俗与契丹相近,后迁潢水以南,与奚族合并,并于唐代末叶俱附契丹。今年,北京地区发现的一些墓志、碑碣中,曾屡见记有“白NB275”籍贯的人物③,反映了辽金两代中国北方多民族交融、流动节奏的加快。 据志文所叙,闲公“幼失所怙”(即失去父亲),而“宿(夙)植善因,蚤(早)慕真谛”,而且十岁便到天庆寺受经业,笔者推定,“白NB275”只是张伟的籍贯,他也许从来就没有在那里居住过,也许在他出生前,张家便移居到燕京(今北京)一带,所以他才能年方十岁便到天庆寺拜师受业。“天庆”即辽天庆寺,据有的研究者考定,始建于辽代,原名弥陀院,清代初年尚存,遗址在今北京天坛西北金鱼池一带④。另外,张家在燕京虽非大族,但张伟能在幼失怙宠的情况下,仍“植善因”、“慕真谛”,并能进寺院受经业、返亲舍读儒书,受到良好的教育,足见其家庭状况与区域人文背景的优越。 铭文赞张伟“才誉籍籍,一举中进士第”,惜未言及其中第的具体时间,这就给今人的考释带来一些困难。但是,细审墓主生平,尚可推测一二。据志文后半部残留有“阅世六十八年”的文字推算,可知张伟应生于辽道宗大安元年(1085年),他10岁入寺院授经业应在辽寿昌元年(1095年),17岁返家读儒书应在辽天祚帝乾统二年(1102年)。志中说他一举中第,虽未及具体年份,但从语境上看,应在“弱冠之年”即20岁之前。如果此说不谬,那么,这位张伟,真可谓朱颜轩冕(服冕乘轩)、少年得志了。 “历官州县,繇北京都市令以选入枢密院通NB332。任职六年,出补香河令。更两考,有能声。先是,民间有冒耕官闲田,公被檄与府官捡括。时夏麦且熟,恐民不得获。既行,涉积水,阳(佯)失辔坠而溺,从者惊援之。及出,即移病归卧,请展期。比愈得报,再行则皆获矣。” 考张伟登进士第后“历官州县”,应是辽朝所辖之州、县,而具体职务,似是判官或县丞一类“佐贰”官。而“北京都市令”之“北京”,似应指辽中京路之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北),因辽无北京之称,金代天眷元年(1138年)改辽上京临潢府为北京,至金贞元元年海陵迁都燕京,改中京路置,改大定府为北京。志文虽叙辽代事,但系金代命官所撰,且书于贞元元年五月,时刚刚改称,所以,此“北京”当指辽之中京大定府。“都市令”,《辽史》与《金史》百官志均不见载,推测当系留守官之属僚。 “枢密院”,亦为辽代之枢密院,而非金代⑤。《辽史》卷四十七百官志三载:“则枢密之设,盖自太宗始矣。”又“汉人枢密院。本兵部之职,……太宗入汴时,因晋置枢密院,掌汉人兵马之政,处兼尚书省。”再据《金史》本纪第二,记金太祖天辅六年(1122年)“上伐燕京,……辽知枢密院左企弓、虞仲文,枢密使曹勇义,副使张彦忠,参知政事康公弼,侍书刘彦宗奉表降”,可知辽末枢密院曾置于燕京。“枢密院通NB332”一职,《辽史》、《金史》百官志均不载,且“NB332”字不能识读,推测可能为“事”的俗体字——如果确为“事”,则“通事”一职见于《金史》百官志一“枢密院”条:“译史三人,通事三人……”。金承辽制,“通事”一职虽失载于辽史,但承辽而置,应不是妄断。枢密院乃要津中枢,能在其中“行走”,通事一职虽微,但也可证年轻的张伟确有“才誉”。 “邑户佃圭田,凡留守要人者,率藉形势免科调。问之,以例对。公曰:‘皆王民也,例谁为者?’一以法令从事,役以故均。而大忤权贵,至檄召诣府,屡加摧□,公执不改,卒依行之。其守如此,累阶至尚书郎。” “圭田”,古代卿大夫祭祀用的田地。《孟子·滕文公上》:“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宋朱熹注:“圭,洁也,所以奉祭祀也。”可知这是事关封建士大夫的一种特权和礼仪,估计圭田也可得免纳赋税的优惠。但据志中所记,当时在中都大兴府各县,这种冒圭田之名而免征事役的土地很多,大都是身居高位的留守要人所有,且弊俗由来已久,官官相护,习以为常。张伟任县令后,则决心革除弊端,“一以法令从事”使“役以故均”。结果是大忤权贵,虽要人以公文形式“召诣”令改,但“公执不改,卒依行之”。不过,据志文所述,张伟的这种行为,虽惹了些烦恼,却未致祸,而“累至尚书郎”。尚书,指尚书省。金之尚书省建于金太宗天会四年(1138年)⑧,是金政权的中枢机构。尚书郎,应是“郎中”或“员外郎”的俗称。据《金史·百官志一》“尚书省”条:“郎中一员,正五品……员外郎一员,正六品,总察吏、户、礼三部受事付事……”可知尚书郎虽然品级不算太高,却是身居要津,总勘全局,可谓处于权力漩涡的中心了。此段志文关于辽、金易代之际,燕京权贵豪门以“圭田”之名,大多“籍形势免科调”的记述,不见于正史,而塔铭补其所阙,尤堪珍视。 “一日,读首楞严经十习六交因报之说,感悟发心,取香三瓣,炷於顶门及两肩。燃之,默祷自誓。又以诗寄平生友人兼平章曰:万缘躁恼丛如发,试看临时下一刀。从此不近妻妾。” “平生友人兼平章”,即为其死后立灵塔者张通古。据《金史·张通古本传》载,金天会四年(1126年),张通古“除工部侍郎,兼六部事”,与张伟有同僚之谊。当时,通古尚非平章,海陵天德初,才“进拜平章政事”;因撰此铭是天德后的贞元年间,故称平章。志中说张伟因读佛经而感悟,厌恶俗世,准备“临时一刀”,斩万根烦恼丝。其实,这只是他遁入空门的起因和心理准备阶段,虽从此不近妻妾,却“犹身为榷盐官”⑨,勤政于国。也许就是在其以尚书省郎中兼榷盐官的这段时间里,由于他“遵於推捡故□”⑩,“疾恶如仇”,得罪了更多的当朝权贵和“奸吏”,也就遇到了更大的障碍和困难,终“抑不能忍”,谓自己“属世多故,复不能委屈轩轾,以徇权势”,所以“慨然欲求出世间,得自拔流俗。”铭志具体描述了张伟弃官出家的过程: “独念老母恩不可报也。来问,跪曰:‘言有为皆幻,惟一大事,可以於尘垢脱出,死愿允耳於亲,归近圣道,以答NB279劳。’母曰:‘汝志如是,吾顾不能耶?’欣悦听许。公拜谢,未几,先命二妻一子相继出家。乃以天会六年正月弃官入鞍山之慧聚寺。亲友闻者争劝止,朝省亦遣人趋召,竟不至。执僧悟柔,自言:‘伟误罹世网,崎岖半生,今喜亲许出家矣!愿从壤削,用道修典,惟师摄受,为我落发。’柔与其徒愕曰:‘府君学有闻,且通朝野,斯言谓何,岂绐我乎?’公曰:‘断之于心久矣,语一出口,天地诸圣实临之。’□选理□斋□诚书之制度。公乃取鞍山先师画像置堂中,焚香作礼,自称门人。而易”(下残)志文简捷而生动地描述了张伟辞亲的过程和入山受戒的细节,其中的一些人物对话很真实,蕴涵也很深,如张自言“属世多故”,自己又不能“委屈轩轾,以徇权势”,则可折射出士子阶层对所处时代的真实看法。这对于研究辽、金两代的佛教史和思想史都是难得的材料。 三、韬光匿影 游锡四方张伟悬崖撒手、入山向佛后的具体行实,在铭中应有记述,但遗憾的是,由于以下两面石刻,磨蚀殆尽,仅存150余字,且只可分行连读,所以难窥其详了。然而,从残存的词句如“上京”、“尝访师之居”、“径山禅师弟子”、“太湖雨道院”、“韬光匿影”、“谒青州希辩禅师”中,可推断张伟受戒后,韬光匿影、游锡四方,广佛法而度世人。 据残留文字“日,趺坐顺化,阅世六十八年”,可知张伟死于海陵贞元元年初,僧寿二十五,其天会六年出家时应为43岁。 四、友人平章张通古 塔铭末尾款署“开府仪同三司平章政事上柱□□□□□□□□张通古建”,标明了墓塔的建立者乃是当朝宰执级的人物。张通古,金初名臣,《金史》纪、传中对其都有记述。张通古字乐之,易州易县(今河北易县)人。辽天庆二年登进士第,补辽枢密院令史;辽、金易代之初,曾一度隐居。金天会三年(1125年)金军收复燕京后,经侍中刘彦宗推荐,召为枢密院主奏,由此仕金。天会四年(1126年)金廷初建尚书省,除工部侍郎,兼六部事。海陵天德初,迁行台左丞,进平章政事,封谭王,改封晖王,复拜司徒,封NB276王。正隆元年(1156年)以司徒致仕,进封曹王;于当年逝世,享年69岁B14。本传中说张“读书过目不忘,该综经史,善属文”,不仅颇富治世经国的才略,而且坚持正义,不惧强权,“天资乐易,不为表NB322,虽居宰相,自奉如寒素焉”。因此,甚得人尊重,连平时御下严厉,亲王大臣未尝少假以颜色的海陵王完颜亮,“惟见通古,必以礼貌”B15。 五、文士右相刘长言 此石幢塔的撰铭者也是金代前期的一位著名的人物,他就是以诗文名世并当过尚书右丞的刘长言。 塔铭中标其职衔为“银青光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其中,“银青光禄大夫”,为文官从二品上,《金史·百官志》:“文官九品,阶凡四十有二……正二品……下曰银青荣禄大夫。从二品上曰光禄大夫”。铭中“光禄”前加“银青”不见于史,待考。“翰林学士承旨”,为正三品,《金史·百官志》:“翰林学士承旨,正三品,掌制撰词命。” 因刘长言撰铭是在贞元元年(1153年)五月,彼时尚未拜相,而其任尚书右丞是在7年后的正隆五年(1160年)了。据史籍记载,刘长言字宣叔,东平人(今山东东平县)。天德三年(1151年)以翰林学士使宋,正隆五年三月,除拜尚书右丞,十一月罢,其父刘NB333,仕至仪真令,工诗文,有《南荣集》行世。长言亦以诗文世其家B16。 六、正隆凿抹 石痕尚存 海陵王完颜亮正隆二年(1157年)二月,诏令“改定亲王以下封爵等第,命置局追取存亡告身,存者二品以上,死者一品,参酌削降。公私文书,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毁抹,虽坟墓碑志,并发而毁之”B18。这是当时海陵王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制的一件重大的政治举措。施行的也十分严厉:削降王爵之号不仅包括活着的人,而且殃及死者;不仅公私文书中涉及王爵字样的必须立即毁掉或抹去,而且连埋在地下的碑志,也要掘出凿毁。今天我们可以推测,以海陵之威,当年这道诏令贯彻的肯定十分彻底,其波及面也一定会很大。那么,死于正隆二年前、又有王爵封号的张通古是否也被殃及了呢? 此塔建于贞元元年,当时通古已进拜平章政事、封NB276王。在金代,平章政事从一品,为宰相,而从一品上是文官品阶,曰开府仪同三司,所以塔铭通古官阶标“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则是勋封正二品B19。以上这些职衔,都与削降王爵的诏令无涉,所以都完好保存至今。但是,不能不写在职衔中的王爵和食邑,却属于应“立限毁抹”的字样,难以保留。今天我们细辩通古职衔铭文,仅存“开府仪同三司平章政事上柱□□□□□□□□张通古建”16个字可识,而中间8个字被人为凿抹掉了。为什么会有人从中间毁去数字?其原因就是这些字表述的应是张通古的王爵和食邑。通古当时封NB276王,其食邑为万户B20。据此,可知被凿抹的8字应是:“国NB276王食邑一万户”B21。 七、小 结 经历了850个寒暑依然兀立于京西燕山的严行大德灵塔,是金代历史文化的宝贵遗存。它精美的造型,是金中都建筑艺术与石雕艺术结合的典范;由金初著名文士刘长言撰写的铭志是一篇情理交融的美文,既生动真实地反映出辽金之际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生活,也代表了金代文学的创作高度;而灵逸疏朗的志文刻写,则形象显示出金初书法的水平B22。特别是正隆二年海陵诏“削降王爵”历史事实在石刻中保留了清晰的痕迹,为同类文物前所未有,其证史作用之巨,不言而喻。总之,这是一件考古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兼俱的重要的历史文物,尤须积极保护、深入研究。 《大金故慧聚寺严行大德闲公塔铭并序》 道无异致 教或因时 会其有极 ①《门头沟文物志》第二章第二节,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为辽金城垣博物馆研究员及馆长和工作人员) |